

具体描述
商品参数
| 新型有机污染物的环境行为 | ||
| 曾用价 | 128.00 | |
| 出版社 | 科学出版社 | |
| 版次 | 1 | |
| 出版时间 | 2018年06月 | |
| 开本 | 16 | |
| 作者 | 王亚韡等 | |
| 装帧 | 圆脊精装 | |
| 页数 | 299 | |
| 字数 | 378000 | |
| ISBN编码 | 9787030574237 | |
内容介绍
2004年11月《斯德哥尔摩公约》正式对我国生效,我国面临履约及削减POPs的巨大挑战,缺乏对我国POPs生态风险评价的基础数据和POPs的基础研究相对薄弱是我国履约及控制POPs环境污染的*大障碍。*近几年,随着国际公约的推动,公约POPs候选物质以及相关物质的研究日益成为环境科学研究的焦点问题之一。本书较系统地介绍了从2009年第四次《斯德哥尔摩公约》缔约方大会会议以来新增POPs的背景信息、分析方法、环境行为以及毒性毒理学效应等方面的研究进展。
目录
目录
丛书序
前言
第1章 引言 1
1.1 新型有机污染物的持久性 4
1.2 新型有机污染物的生物富集性/放大性 8
1.3 新型有机污染物的长距离迁移能力 9
1.4 中国《国家实施计划》 14
1.5 未来研究的重点 14
参考文献 16
第2章 多溴二苯醚(PBDEs)研究进展 21
2.1 化学特性 22
2.2 环境来源 23
2.3 分析方法 25
2.3.1 样品前处理 25
2.3.2 填料及配制 27
2.3.3 仪器分析 30
2.3.4 PBDEs色谱分析应用实例——高分辨气质联用法 37
2.4 环境归宿 45
2.4.1 持久性 46
2.4.2 远距离迁移能力 47
2.4.3 生物富集性 47
2.5 环境暴露 49
2.5.1 环境浓度水平和趋势 49
2.5.2 人类接触 52
2.6 健康效应 55
2.6.1 水生生物毒性效应 55
2.6.2 鸟类和哺乳动物的毒性效应 56
2.6.3 其他生物毒性效应 58
2.6.4 生物积累和生物放大作用 58
2.7 十溴二苯醚的降解和脱溴作用 59
2.8 总结 62
参考文献 63
第3章 全氟化合物(PFASs)研究进展 76
3.1 PFASs概述 77
3.2 PFASs分析方法 79
3.2.1 样品前处理方法 79
3.2.2 仪器分析方法 80
3.2.3 异构体分析方法 80
3.3 PFASs的环境分布 82
3.3.1 水体 82
3.3.2 沉积物 84
3.3.3 土壤 86
3.3.4 大气 87
3.3.5 异构体环境分布 89
3.4 PFASs的生物累积与毒性效应 90
3.4.1 生物累积与生物放大 90
3.4.2 毒理学研究 92
3.5 人体PFASs暴露及健康风险 94
3.5.1 人体暴露水平 94
3.5.2 排泄与半衰期 96
3.5.3 暴露量与暴露途径 97
3.5.4 健康风险 98
3.6 新型PFASs研究进展 100
3.7 PFASs污染控制技术与限制条款 102
3.7.1 PFASs污染控制技术 102
3.7.2 国际上的控制与监管 102
3.8 总结与展望 103
参考文献 103
第4章 短链氯化石蜡(SCCPs)研究进展 118
4.1 物理化学性质 119
4.2 来源、使用和释放 119
4.3 分析方法 120
4.3.1 样品前处理 121
4.3.2 仪器与定量分析 126
4.4 环境水平及污染现状 133
4.4.1 空气 133
4.4.2 表层水、河水和湖水 134
4.4.3 污水处理厂污水 134
4.4.4 土壤、底泥以及沉积物 135
4.4.5 生物体 136
4.4.6 人体母乳、食品、灰尘等其他环境介质 137
4.5 环境影响 138
4.5.1 持久性 138
4.5.2 生物富集能力 139
4.5.3 远距离环境迁移潜力 140
4.5.4 毒性效应 141
4.6 研究案例 142
4.6.1 材料和方法 142
4.6.2 结果与讨论 144
4.6.3 小结 155
4.7 总结 155
参考文献 156
第5章 硫丹研究进展 164
5.1 硫丹概述 164
5.2 环境样品前处理及分析技术 166
5.2.1 样品前处理 167
5.2.2 仪器分析技术 169
5.3 硫丹的环境浓度及归趋行为 170
5.3.1 我国硫丹的使用和排放清单 170
5.3.2 硫丹的排放与残留清单 172
5.3.3 我国大气和土壤中硫丹浓度水平和分布 173
5.3.4 硫丹的环境归趋行为 175
5.4 硫丹的毒理效应研究 184
5.4.1 对生物的危害影响 184
5.4.2 对人类健康的影响 187
5.5 硫丹使用的限制公约 188
参考文献 189
第6章 六溴环十二烷(HBCDs)研究进展 198
6.1 HBCDs的结构特点、物理化学性质及毒性效应 198
6.1.1 结构特点 198
6.1.2 物理化学性质 199
6.1.3 毒性效应 200
6.2 HBCDs的生产和使用 201
6.3 HBCDs污染的来源 202
6.3.1 环境中HBCDs的污染源 202
6.3.2 人体中HBCDs的污染源 203
6.4 HBCDs的环境行为 204
6.4.1 在空气中的环境行为 204
6.4.2 在生物体中的环境行为 205
6.4.3 在水和底泥中的环境行为 206
6.5 HBCDs的分析方法 207
6.5.1 样品前处理方法 207
6.5.2 仪器分析技术 210
6.6 环境中HBCDs的赋存状况 214
6.6.1 在大气中的分布 214
6.6.2 在水、沉积物、污泥以及土壤中的分布 216
6.6.3 生物态环境介质中HBCDs的分布 217
6.6.4 HBCDs污染的空间变化趋势 218
6.6.5 HBCDs污染的时间变化趋势 219
6.7 总结 220
参考文献 221
第7章 六氯丁二烯(HCBD)研究进展 233
7.1 HCBD的结构特点、物理化学性质及毒性效应 233
7.1.1 结构特点及物理化学性质 233
7.1.2 毒性效应 234
7.2 HCBD的生产、使用及污染来源 234
7.3 HCBD的环境行为 236
7.3.1 在空气中的环境行为 236
7.3.2 在生物中的环境行为 236
7.3.3 在水和沉积物以及土壤中的环境行为 237
7.4 HCBD的分析方法 238
7.5 我国环境中HCBD的赋存状况 240
7.6 人体暴露HCBD风险评估 243
7.7 土壤中HCBD赋存及风险评估实例 244
7.7.1 样品采集与预处理 244
7.7.2 样品前处理与仪器分析 245
7.7.3 质量控制与质量保证 245
7.7.4 江苏一化工厂厂区及周边土壤中污染水平与分布特征 246
7.7.5 化工厂厂区土壤中HCBD的风险评估 247
7.8 控制措施 249
7.9 研究展望 250
参考文献 250
第8章 得克隆(DP)及其类似物 256
8.1 概述 256
8.2 得克隆及其类似物的生产、使用以及限制情况 258
8.2.1 得克隆在国内外的生产、使用情况 258
8.2.2 得克隆在国内外的限制情况 259
8.3 得克隆的POPs特性 259
8.3.1 得克隆的持久性 259
8.3.2 得克隆的长距离迁移能力 260
8.3.3 得克隆的生物富集性 261
8.3.4 得克隆的毒性 269
8.3.5 得克隆的环境转化 270
8.3.6 小结 271
8.4 我国与世界各地环境及人体中得克隆浓度分布 272
8.4.1 生产地周边环境得克隆浓度分布 272
8.4.2 电子垃圾拆解地得克隆环境浓度分布 272
8.4.3 在污染源以外地区DP浓度分布 273
8.4.4 世界及我国不同区域人体中得克隆浓度分布 274
8.5 我国典型地区得克隆的风险简介 275
8.5.1 得克隆环境风险概述 275
8.5.2 工厂周边地区得克隆环境风险 277
8.6 研究案例——职业暴露人群血液和头发中得克隆浓度水平 277
8.6.1 材料与方法 277
8.6.2 结果与讨论 280
8.6.3 小结 286
参考文献 286
附录 缩略语(英汉对照) 294
索引 298
彩图
在线试读
第1章 引言
本章导读
简述有关POPs的《关于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斯德哥尔摩公约》(以下简称《斯德哥尔摩公约》)有关背景,阐释POPs的四大特点以及公约运行机制。
简述《中华人民共和国履行〈关于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斯德哥尔摩公约〉国家实施计划》(以下简称《国家实施计划》)。
展望未来有关新型有机污染物的研究热点。
持久性有机污染物(persistent organic pollutants,POPs)是指在环境中难降解、高脂溶性、可以在食物链中富集放大,且能够通过各种传输途径而进行全球迁移的半挥发性且毒性极大的污染物。由于其污染的严重性和复杂性远超过常规污染物,*近数十年已成为环境科学研究的热点。POPs由于具有“三致”(致畸、致癌、致突变)效应,并且其危害具有隐蔽性和突发性的特点,一旦发生重大污染事件,将会产生灾难性后果甚至会持续危害几代人。
*近一百年来,国际上环境保护经历了从常规大气和水污染[如氮氧化物、粉尘、化学需氧量(chemical oxygen demand,COD)、生化需氧量(biochemical oxygen demand,BOD)]治理、重金属污染控制到POPs削减与控制的历程。2001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通过了旨在保护全球人类免受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危害的《斯德哥尔摩公约》。目前已经有包括我国在内的179个国家或地区加入了该公约,从缔约方数量上不仅能看出《斯德哥尔摩公约》的国际影响力,同时也能看出全世界对于POPs污染的重视。该公约规定的12种POPs如艾氏剂、氯丹、滴滴涕、狄氏剂、异狄氏剂、七氯、六氯苯、多氯联苯、灭蚁灵、毒杀芬、多氯代二苯并-对-二英、多氯代二苯并呋喃被称为“肮脏的一打”(dirty dozen)而受到了各缔约方的严格控制与削减。在《斯德哥尔摩公约》的推动下,国际上有关POPs的相关研究逐步深入,已成为环境科学研究中*受人们关注的热点领域之一。
《斯德哥尔摩公约》新增列或拟增列及国际学术界高度关注的有机污染物通常称为新型POPs。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全球化学品展望》(2012年发布)指出,持久性有毒物质污染了整个地球。这些物质既包括传统污染物如经典POPs、重金属等,也包括新型有机污染物如卤系阻燃剂、全氟化合物(perfluoroalkyl substances,PFASs)等。而随着人类经济活动的快速发展,这些新型有机污染物也不断地从各种环境介质中被发现而成为环境科学研究的热点。这些新型POPs在我国具有以下特征:①绝大多数为目前正在大量生产和使用的化工产品,尚未对其生产环境排放进行有效控制;②污染正在发生,并且在环境介质中的存量较高,但对其源和汇仍缺乏认知;③有关生态风险、健康风险和毒理学的数据还较为缺乏,难以准确评估其生态效应和健康效应。目前,国际上环境科学对新型POPs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两部分工作:一部分工作是对公约秘书处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审查委员会(POPRC)名单中新增POPs和正在接受审查的新型POPs物质进行研究;另一部分工作是对于未知有机污染物在环境介质中的鉴别及定量分析。
国际上对新型POPs的研究起步较早,对于其有关环境行为、归趋以及对人体健康风险的评价已有较深入的认识。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目前面临着更为复杂的环境问题。鉴于新型POPs的巨大累积产量,我国新型POPs所引起的环境污染和健康风险问题比其他国家更为严重,尤其是在我国东部经济发达地区。在常规污染及重金属污染尚未得到有效控制的同时,POPs的污染及控制也是我们目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难题。在初步解决了滴滴涕、六六六等经典POPs的环境污染问题后,短链氯化石蜡(short chain chlorinated paraffins,SCCPs)、卤代阻燃剂等新型POPs又成为我国环境面临的新问题。在我国一些区域可食用水产品中已检测到较高含量的多溴二苯醚(polybrominated diphenyl ethers,PBDEs)(Zhu et al.,2012),而电子垃圾拆解的溴代二英、PBDEs 以及其他溴代阻燃剂造成的环境污染也十分严重,所导致的环境问题也已经引起了国际关注(Ni and Zeng,2009;Wu et al.,2011)。对于PFASs的研究表明,我国人体血液中全氟辛基磺酸(perfluoroctane sulfonic acid,PFOS)的含量明显高于日本、韩国、波兰等国(Yeung et al.,2006),而在生产企业的职业暴露人群中,人体血样中PFOS的含量和美国3M 公司职工血样中含量相当(Gao et al.,2015)。基于国内相关研究成果和作为国际公约履约行动的一部分,2014年3月25日环境保护部联合其他11部委发布“《关于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斯德哥尔摩公约》新增列9种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关于附件A、附件B和附件C修正案》和新增列硫丹的《关于附件A修正案》生效的公告”,提出其将自2014年3月26日对我国生效,要求在全国范围内加强新增列POPs的管理及风险防范。
《国家环境保护“十二五”科技发展规划》在“全球环境问题研究领域”中围绕全球环境变化和国际履约问题,指出要提升我国履行国际环境公约的能力,强调开展典型行业POPs排放、检测与表征方法学研究,进而开展我国典型区域POPs来源、污染水平与特征、迁移转化规律、削减与控制技术以及风险评估的相关研究。《国务院关于加强环境保护重点工作的意见》提出要加强POPs排放重点行业监督管理。《全国主要行业持久性有机污染物污染防治“十二五”规划》中也要求加快建立POPs污染防治标准体系,强调开展POPs及其前体物在环境中的迁移转化及健康风险研究。
我国是《斯德哥尔摩公约》的缔约方之一,这体现了我国政府对全球环境保护的重视。目前我们仍然面临巨大的挑战,作为化学品生产和使用大国,对于新型POPs在化学品管理、环境行为、生态毒理乃至环境风险方面仍然缺乏关键数据和科学研究基础。但是,通过设立相关的科研项目、建立相应的专业实验室,已经大大提高了对于POPs特别是新型POPs的检测水平和能力,并开展了新型POPs的主要污染源、排放因子、污染特征及演变趋势等方面的研究,同时随着履约工作目标的不断增加和更新,对新型POPs的研究内容也在不断地调整和更新。
对于新型有机污染物,目前环境科学研究的焦点问题即其持久性、生物富集/放大性、长距离迁移性以及生态毒性。《斯德哥尔摩公约》规定了任一缔约方均可向秘书处提交旨在将某一化学品(拟增列POPs)列入公约附件A、B和/或C的提案。而公约秘书处将提案转交给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审查委员会(POPRC)后,将依次对其与公约附件D即对化学品的持久性、生物富集性、长距离迁移能力及不利影响进行评价,附件E即评价该化学品是否会因其远距离迁移而对人体健康和/或环境产生重大不利影响进行评价,附件F即涉及社会经济考虑因素的信息是否符合公约对POPs的要求,如果全部符合,审查委员会将根据风险管理评价的结果提议是否由缔约方大会审议该化学品以便将其列入附件A、B和/或C并规定相应的管理措施。图1.1为POPRC 针对某一候选物质的审查流程。
2009年5月在瑞士日内瓦举行的缔约方大会第四次会议决定将全氟辛基磺酸及其盐类以及全氟辛基磺酰氟、商用五溴二苯醚、商用八溴二苯醚、开篷、林丹、五氯苯、α-六六六、β-六六六、六溴联苯等九种化学物质新增列入《斯德哥尔摩公约》附件A、B和/或C的受控范围。2011年缔约方大会第五次会议、2013年缔约方大会第六次会议以及2015年缔约方大会第七次会议又分别决定将硫丹及硫丹硫酸盐、六溴环十二烷、多氯萘、六氯丁二烯及五氯苯酚等物质增列为公约POPs名单。2017年5月缔约方大会第八次会议将SCCPs、十溴二苯醚以及六氯丁二烯正式增列为公约POPs新增名单。目前正在进行审查的化学品包括全氟辛酸及相关物质、全氟己基磺酸盐及其盐类以及相关物质和三氯杀螨醇。
图1.1 POPRC审议新增POPs流程图
1.1 新型有机污染物的持久性
根据《斯德哥尔摩公约》附件D的规定,凡是某一污染物在水中的半衰期大于2个月,或在土壤中的半衰期大于6个月,或在沉积物中的半衰期大于6个月以及其他证据证明该化学品具有其他高度持久性的特性,都可认为该化学品符合POPs有关持久性的标准。
目前,在全球范围内的大气、水、土壤/沉积物、植物等环境介质中都可检测到POPs物质(Jones and de Voogt,1999)。其中,“环境持久性”是POPs*重要的特性之一,是界定一种物质是否算作持久性有机污染物以及筛选新型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重要判据之一,也是评价有机污染物对人类和环境潜在危害的基础以及开展化学品风险评估的关键依据(张焘等,2012)。2009年,《关于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斯德哥尔摩公约》的附件D规定,持久性的评价标准为:对于通过空气大量迁移的化学品,其在空气中的半衰期应大于两天,或者该化学品在水中的半衰期大于两个月,或在土壤/沉积物中的半衰期大于六个月;或该化学品具有其他足够持久性,因而或可考虑将之列入本公约适用范围的证据。
常见的《斯德哥尔摩公约》中受控POPs在不同介质(大气、水、土壤)中的半衰期总结见表1.1。POPs的持久性可以影响POPs的其他特性。对于在环境中释放速率一定的化学品,持久性等化学性质将决定其在大气、水、土壤等各环境介质中的浓度。由于持久性化学品在环境与生物体中消除更慢,因此其在环境与生物体中存在的时间更长(Jones and de Voogt,1999)。多种化学品的持久性与其生物富集、长距离迁移能力的相关性研究表明,一般而言,有机污染物的持久性越强,越难化学与生物降解,因此其生物富集性和长距离迁移能力也越强(Rodan et al.,1999)。公约首批12种POPs的持久性总体上较强,其也显示出更强的生物富集和长距离迁移能力。对于亨利常数大于0.001 Pa·m3·mol-1 的化学品,大气中的半衰期是决定其长距离迁移能力的关键因素,可用化学品在大气中的半衰期对其长距离迁移能力进行简单筛选。POPs的持久性(低化学/生物反应性)导致其具有较强的生物富集及较高的内暴露浓度,这种长期暴露也可能引发对生物更强的毒性。
鉴于POPs的持久性所引发的一系列环境问题,应对其相关问题进行深入研究。①POPs持久性评价技术:相对于POPs在分析方法、环境归趋等方面的大量研究,针对有机污染物持久性的量化评价方法的研究还较少。未来应进一步综合采用定量结构-活性/性质相关性(quantitative structure activity relationship/quantitative structure property relationship,QSAR/QSPR)方法、环境多介质模型方法以及分子反应性方法对POPs持久性进行更为准确的定量评价(张焘等,2012)。②高效POPs化学/生物降解与替代技术:POPs通常难以化学与生物降解,因此亟需利用新的化学/生物降解机理,发展可应用于POPs在排放过程及多种环境介质中的高效POPs化学/生物降解技术(如基因工程菌),同时寻找更为绿色、安全、有效的POPs的化学品替代品,从排放源头至环境介质,多线并举,减少POPs的排放与环境赋存。③极地与偏远地区(如青藏高原)POPs的传输与累积:极地与偏远地区POPs人为直接排放少,是研究POPs长距离传输的理想地区。此外,这些区域生态较为脆弱,POPs传输与累积可能造成更为显著的环境影响。应加强POPs的多尺度(局域尺度、大陆尺度、大洋尺度、全球尺度)、多途径长距离传输(大气传输、洋流传输、鱼类洄游传输、鸟类迁徙传输)与累积研究,更好地理解POPs的来源和受体地区、POPs传输通道以及相关的土-气、水-气交换和分配过程。④环境介质中POPs的再释放问题: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人为活动向环境中释放了大量POPs,POPs在底泥、林地土壤等介质中有显著累积。由于《斯德哥尔摩公约》的实施,POPs的人为排放显著减少。但POPs的多介质分布与环境变化(如温度、土地利用变化)可能引发环境介质中POPs再释放问题。例如,森林叶片吸收大气POPs,叶片凋落物引起林地土壤积累POPs;在林地转换为耕地等土地利用变化过程中,可能导致原有林地土壤中POPs的再释放。⑤POPs的代际传递问题:胚胎及新生儿阶段是个体发育的关键时期。由于胚胎及新生个体对化学污染物的暴露较母体更为敏感,因此应系统开展多种POPs通过胎盘、母乳对胎儿、新生儿的代际传递研究,从而科学评价POPs的环境与健康风险。
表1.1 常见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半衰期
用户评价
这本书的封面设计得非常引人注目,那种深邃的蓝色调,配上简洁的几何图形,一下子就把人带入了一种严谨而又充满探索感的氛围中。我原本是抱着了解一些基本概念的心态翻开的,毕竟“新型有机污染物”这个名词听起来就挺高深的。然而,初读几页,我就被作者那种深入浅出的叙事方式所吸引。他似乎有一种魔力,能将那些复杂的化学反应和生态学机制,用生活化的语言娓娓道来。比如,他对某些新型表面活性剂在水体中的迁移路径的描述,简直就像在看一部微观世界的探险记,充满了悬念和对未知的敬畏。我尤其欣赏的是,作者没有停留在理论的堆砌,而是不断地将抽象的概念与我们日常生活中接触到的具体产品联系起来,这让阅读过程充满了“原来如此”的顿悟时刻。它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去看待我们习以为常的消费品,从它们的诞生到最终的归宿,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令人深思的循环链条。这本书的结构安排也非常合理,循序渐进,让人在不知不觉中吸收了大量前沿信息,完全没有传统教科书那种枯燥乏味的感觉。
评分这本书的编排结构对于希望建立知识体系的读者来说,简直是一大福音。它不像某些零散的文章汇编,而是构建了一个逻辑自洽的知识网络。从基础的分子特性分析,到宏观的环境归趋模型,再到最后的生态毒理学评估,每一个章节都像是一块精雕细琢的积木,紧密地嵌合在一起,形成一个坚实的整体。我发现,即便是跨越不同污染物类别的讨论,作者也能找到一个共同的理论支点进行连接,这极大地帮助我系统地理解了“新型有机污染物”这一大类物质的共同挑战。更实用的是,书中对当前国际上主要的监管框架和监测技术也有详尽的介绍。这使得这本书的价值不仅仅停留在理论层面,还具有极强的实践指导意义。对于环境工程师或政策制定者而言,这本书无疑是一份极具参考价值的案头必备读物,它提供了理解问题和寻求解决方案所需的全面视角和深度支撑。我强烈推荐给任何对未来环境质量抱有责任感的人。
评分这本书的排版和装帧质量绝对是顶级水准,拿在手里有一种沉甸甸的厚实感,这无疑提升了阅读体验。更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作者在行文过程中大量引用的图表和数据可视化处理得极其精妙。那些复杂的浓度梯度图、半衰期曲线,不再是晦涩难懂的线条堆砌,而是变成了清晰的视觉语言,有力地支撑了作者的论点。我记得有一章专门讨论了某些新兴内分泌干扰物在食物链中的富集效应,书中用了一张层级递进的插图,将这个生态风险的放大过程描绘得淋漓尽致,那种视觉冲击力远胜于单纯的文字描述。对于需要深入理解污染物迁移机制的专业读者来说,这些详实的图表简直是福音,它们是理解复杂环境过程的“捷径”。当然,即便是对环境科学了解不深的普通读者,也能从中感受到科学的严谨性和对环境问题的重视程度。这本书的每一个细节,似乎都在向读者传达一种信息:我们所讨论的,是经过严格验证的真实世界问题。
评分我发现这本书最难能可贵的一点在于它的批判性思维的引导。作者并非一味地介绍“新污染物”,而是深入剖析了“新”背后的驱动力——社会需求、技术进步与环境监管滞后之间的张力。在探讨某些新型阻燃剂的替代品时,作者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我们是否总是在用一种我们尚不完全了解的风险,去替代另一种已被我们熟知的风险?这种哲学层面的反思贯穿始终,迫使读者跳出技术解决问题的窠臼,从更宏观的系统角度去审视人类活动与自然环境的互动关系。阅读这本书的过程,更像是一场与作者进行的高水平智力对话,他不断地提出挑战性的观点,然后引导我们去寻找证据,去构建自己的认知框架。它不仅仅是一本知识传递的书,更像是一份激发独立思考的“工具箱”。我合上书本时,脑海中充满了关于可持续化学和绿色设计的思考,这远超出了我对一本科普或专业参考书的预期。
评分这本书的语言风格有一种独特的沉稳力量,它不像某些学术著作那样充满佶屈聱牙的术语,也不同于纯粹的科普读物那样过于轻快。作者的语气始终保持着一种深思熟虑的、近乎历史学家的口吻,去记录和分析这场正在我们身边发生的,关于化学物质与地球环境的较量。我尤其欣赏作者在论述那些尚未被充分研究的污染物时所展现出的审慎态度。他从不妄下断言,而是清晰地勾勒出当前研究的空白地带,并指出未来需要重点关注的方向。这种“已知与未知”的边界描绘,给人的感觉非常真实可信。他没有将环境问题简单化为“好与坏”的对立,而是展现了一个充满灰色地带的复杂现实。这种对复杂性的接纳和尊重,让这本书的论述显得格外有分量,也让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建立起了一种对科学研究的敬畏感,理解真正的科学探索是多么的艰难而又至关重要。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内容均为互联网搜索引擎提供的公开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储任何数据与内容,任何内容与数据均与本站无关,如有需要请联系相关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于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6 book.cndgn.com All Rights Reserved. 新城书站 版权所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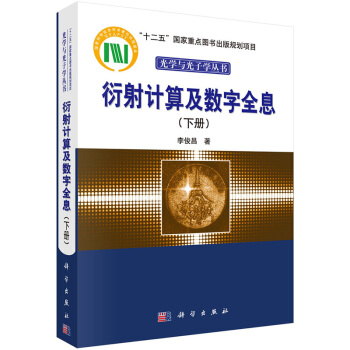






![生物学与生活(原书第10版) [Biology: Life on Earth, 10e]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qciss.net/12035094/57d829caN6aa98a9c.jpg)


![城市化 城市地理学导论(原书第3版) [Urbanization: An Introduction to Urban Geography,]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qciss.net/11902077/57075414Nf926c295.jpg)
![[按需印刷] 理论计算与模拟在光催化研究中的应用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qciss.net/1652373959/55b4d3feN9494c891.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