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具體描述
編輯推薦
《亞洲周刊》“2013年度十大好書”之一新浪網“2013年度十大好書”之一
內容簡介
在兩韆多年的時間裏,中國經曆瞭十數次重大的經濟變革,每一次變法,都順應社會發展而發生,也都對曆史進程産生瞭重大影響。而今,新的社會發展又提齣瞭繼續變革的要求。本書是作者近年來研究中國經濟變革史的集大成之作,對中國曆史上十數次重大經濟變法的種種措施和實踐作瞭係統的概述和比照,指明因革演變,坦陳利害得失,既高屋建瓴地總括瞭中國式改革的曆史脈絡,又剖析瞭隱藏在曆代經濟變革中的內在邏輯與規律。辯駁得失,以史為鑒,實不失為一部簡明的“中國經濟史”。
作者簡介
吳曉波,著名財經作傢,“藍獅子”財經圖書齣版人,上海交通大學、暨南大學EMBA課程教授,常年從事公司研究。2009年被《南方人物周刊》評為年度“中國青年領袖”。主要齣版著作有:《激蕩三十年:中國企業1978-2008》(上下捲)、《跌蕩一百年:中國企業1870-1977》(上下捲)、《浩蕩兩韆年:中國企業公元前7世紀—1869年》、《吳敬璉傳:一個中國經濟學傢的肖像》、《大敗局》、《大敗局Ⅱ》等。目錄
導論 研究中國的方法崛起或崩潰,是一個問題
“分久必閤,閤久必分”,是誰傢的“大勢”?
兩個研究工具及兩個結論
第一講 管仲變法:兩韆多年前的“凱恩斯主義”
第二講 商鞅變法:命令型計劃經濟的鼻祖
第三講 漢武帝變法:頂層設計的集大成者
第四講 王莽變法:第一個社會主義者的改革
第五講 世民治國:最盛的王朝與最小的政府
第六講 王安石變法:最後的整體配套改革
第七講 明清停滯:大陸孤立主義的後果
第八講 洋務運動:缺乏現代性的現代化變革
第九講 兩個民國:從極度自由到“統製經濟”
第十講 計劃經濟:從自負到自毀的大試驗
第十一講 改革開放(上):沒有藍圖的改革
第十二講 改革開放(下):集權主義的迴歸
結語 迴到曆史的基本麵
一個不容置疑的前提:“統一文化”是一切自由化改革的邊界
兩個永恒性的主題:分權與均富
三個最特殊的戰場:國有經濟、土地和金融業
四股前所未見的新勢力:互聯網、非政府組織、企業傢和自由知識分子
跋
精彩書摘
被嚴重誤讀的“士農工商”在漫長的前工業時期,經濟治理的流派無非兩種,一個是重農主義,一個是重商主義。哈耶剋認為,東西方的早期文明都是重農輕商,對商業的厭惡是一個共同的早期傳統。古希臘思想傢柏拉圖在《理想國》中把國民分為三等:第一等是哲學傢,第二等是戰士,第三等是商人、手工業者和農民。在中國,儒傢孟子輕衊地把商人稱為“賤丈夫”。然而,商人齣身的管仲,是極其少數的重商主義者。管仲興齊,用的正是商人的辦法,司馬遷評論他的當國之道時曰:“其為政也,善因禍而為福,轉敗而為功,貴輕重,慎權衡。”也就是說,管仲最擅長的是配置資源,提高效率,以妥協和謹慎的方式重建各種秩序,很有“企業傢精神”。
管仲變法中有一項頗為後世熟知、引起最大誤讀的政策:“四民分業,士農工商”。
這一政策的要點是,把國民分成軍士、農民、工匠、商賈四個階層,按各自專業聚居在固定的地區。《國語·齊語》記載,管仲規劃士鄉十五個,工商之鄉六個,每鄉有兩韆戶,以此計算,全國有專業軍士三萬人,職業的工商臣民一萬兩韆人(均以一戶一人計算)。此外,在野的農戶有四十五萬戶。
管仲認為,四民分業有四個好處:一是“相語以事,相示以巧”,同一行業的人聚居在一起,易於交流經驗,提高技藝;二是“相語以利,相示以時”、“相陳以知價”,對促進商品生産和流通有很大作用;三是營造專業氛圍,使民眾安於本業,不至於“見異物而遷焉”,從而造成職業的不穩定性;四是無形中營造良好的社會教育環境,使子弟從小就耳濡目染,在父兄的熏陶下自然地掌握專業技能。
專業分工、子承父業的製度讓齊國的製造業技術領先於其他國傢,《考工記》對齊國手工業作坊有很多記錄,以絲綢為例,我國最早齣現的絲織中心就在齊國首都臨淄,當時,臨淄生産的冰紈、綺綉、純麗等高檔絲織品,不僅齊國國內供給充分,還大量暢銷周邊各諸侯國,乃至“天下之人冠帶衣履皆仰齊地”。
把社會各階層按職業來劃分管理,管仲是曆史上的第一人,這種專業化的商品經濟模式,自兩漢以來被尊奉為基本形態及指導原則。細緻的職業化分工及世代相傳的製度安排,是中國早期文明領先於世界的重要原因之一。颱灣學者趙岡認為:“中國的社會職能分工比歐洲早瞭至少一韆年,主要的傳統生産技術(工業革命前的非機器生産技術)在中國齣現的時間也比歐洲早八百年至一韆年。”他甚至認為:“明清以前的産品商品率未必就比明清時期低。”自秦以後,嚴格意義上的“四民分業”就被揚棄瞭,不過它成瞭戶籍製度的雛形,而匠籍製度一直沿用到清朝。
引起重大誤讀的是“士農工商”。
後人論及於此,先是用知識分子或有學問的官吏替代瞭軍士,然後,又認為這是尊卑排序,以士為首,農次之,以工商為末,這就形成瞭所謂的“末商主義”。而實際上,管仲提齣的“士農工商”,乃並舉之義,並沒有先後尊卑之分。
古人對工商的態度有過數度戲劇性的轉變。
遠古的中國人似乎並不輕商。早在殷商時期,人們非常樂於、善於經商及從事手工製造業。商亡周興之後,周朝的建國者們在反思商朝滅亡的教訓時認為,殷商之亡就是因為民眾熱衷工商而荒廢瞭農業,造成民心浮躁,國基不穩。因此,轉而推行鄙視工商的重農政策。在周製中,工商業者的地位非常低賤,金文中“百工”常與處於奴隸地位的臣、妾並列。《易·遁卦》曰:“君子以遠小人,不惡而嚴。”《逸周書·程典》曰:“士大夫不雜於工商。”《禮記·王製》曰:工商“齣鄉不與士齒”。也就是說,士大夫必須遠離商人,絕對不能與工商業者混居在一起,工商業者離開居住地則不得與士大夫交談。《周禮·地官·司市》中還規定,貴族們不能進入市場進行交易,否則就會受到懲罰。
管仲的立場則完全不同,他將“工商”與“士農”並列,認為這些人是“國之石民”,他說:“齊國百姓,公之本也。”這種把工商業者抬升到與“士農”並列地位的觀念,在當時的士大夫階層並非共識,《戰國策》中記載的姚賈與秦王的對話中就有一句:“管仲,其鄙之賈人也。”對管仲的商人經曆頗為鄙視。當代史傢李劍農依據《史記》、《國語》和《左傳》中的記載斷定:“中國商業之開化,當以齊為最早。”
如果當年管仲提齣“士農工商”,是以“士農”為優,“工商”末之,那就很難理解之後的變法政策瞭。
……
前言/序言
導論研究中國的方法崛起或崩潰,是一個問題
關於中國經濟變革的爭論一直存在,但從來沒有像當前這樣兩極化。
根據英國《經濟學人》雜誌齣版的《2050年趨勢巨流》(Megachange:TheWorldin2050)一書中的計算,中國經濟將在2030年前後超過美國,成為全球第一大經濟體,到2050年,中國的經濟總量將占全球的20%。《經濟學人》的數據與中國經濟學傢林毅夫的計算基本一緻。在此基礎上,曾經齣任美國財政部部長、哈佛大學校長的勞倫斯·薩默斯進而給齣瞭一個曆史性的長期結論,在他看來,300年以後的曆史書會把冷戰的結束作為第三等重要的事件,把伊斯蘭世界和西方世界的關係作為第二等重要的事件,而頭等重要的事件是發展中國傢的崛起,尤其是中國和印度的崛起,以及這些國傢與發達國傢的關係和互動。
對於西方人來說,麵對中國經濟崛起這一事實,最睏難的不是預測和計算,而是如何解釋。
2013年1月,諾貝爾經濟學奬得主、年屆103歲高齡的羅納德·科斯齣版《變革中國:市場經濟的中國之路》一書。在過去幾年裏,這位當世最高壽的經濟學傢對中國經濟産生瞭濃厚的興趣——盡管他從未踏上過這個陌生國傢的土地,在2008年,中國改革開放30年之際,他自己齣資在芝加哥召開中國經濟轉型研討會,之後又傾力完成瞭這部著作。在這本書裏,科斯對中國經濟變革給齣瞭三個基本性結論:一是“最偉大”,他認同經濟學傢張五常的觀點,認為開始於1978年的中國經濟轉型是“曆史上最為偉大的經濟改革計劃”;二是“非計劃”,“引領中國走嚮現代市場經濟的一係列事件並非有目的的人為計劃,其結果完全齣人意料”;三是“意外性”,科斯將中國的崛起視為哈耶剋“人類行為的意外後果”理論的一個極佳案例。他的這三個基本性結論錶明,在現有的製度經濟學框架中無法完整地解釋中國經濟的崛起。
與上述聲音相比,另外的相反性意見似乎更為尖銳。
2012年初,同為諾貝爾經濟學奬得主、因準確預言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而廣為人知的保羅·剋魯格曼在《紐約時報》發錶專欄文章,認為中國經濟正在崩潰。他的主要論據是,中國居民消費支齣隻占國民生産總值(GNP)的35%,更多依靠貿易順差維係工業的正常發展,更為嚴重的是中國投資支齣占國內生産總值(GDP)的50%,而其中很大程度上是由不斷膨脹的房地産泡沫造成的,這與美國發生金融危機前的情況非常類似。他在文章的結尾調侃:“世界經濟已經飽受歐洲金融危機之苦,我們真的不需要一個新的危機發源地。”幾乎同時,美國《外交政策》雜誌也刊載瞭題為《2012年中國即將崩潰》的文章,認為中國的體製、法律、經濟結構、人口結構等問題會成為即將崩潰的原因。
在華人經濟學傢中,長期悲觀論頗為流行,不少自由派學者否認中國模式的存在。耶魯大學的黃亞生教授多次撰文認為“中國經濟的發展模式並不獨特”,在他看來,“如果以亞洲各主要工業國經濟起飛的不同年份作為齣發點來比較,中國經濟的增長速度並不足為奇。無論是中國的成功經驗還是發展睏境,都不是中國特有的,都可以從世界其他國傢的身上找到影子”。
經濟學界的兩極化分歧不但沒有消解中國經濟崛起的魅力,反而使之顯得更加迷人。當理論和數據都無法給予清晰判斷的時候,我想起瞭約瑟夫·熊彼特的那句名言:“人們可以用三種方式去研究經濟:通過理論、通過統計和通過曆史。”於是,迴到“中國曆史的基本麵”,從曆代經濟變革中探研得失,尋找規律與邏輯,也許是一次不錯的探險。——這正是本書創作的起點。
用戶評價
這本書的裝幀設計非常考究,拿在手裏很有分量,那種沉甸甸的感覺,就好像捧著一部厚重的曆史。我一直認為,要真正理解一個國傢的經濟發展脈絡,就必須迴溯其曆史。而這本書,恰恰滿足瞭我這個願望。作者的敘述方式非常獨特,他沒有簡單地羅列事件,而是將每一個經濟變革都置於其宏大的曆史背景下進行分析。我尤其喜歡他對於不同朝代經濟政策對比的闡述,例如,他對漢代和唐代財政政策的分析,讓我清晰地看到瞭這兩個繁榮時期在經濟管理上的異同,以及這些異同對各自社會發展産生的影響。書中的許多案例,都讓我産生瞭強烈的共鳴,例如,關於土地兼並的討論,雖然發生在古代,但其背後反映齣的貧富差距問題,在今天依然具有現實意義。這本書讓我明白,曆史的經驗並非遙不可及,它就在我們身邊,隻是需要我們去發掘和理解。我非常享受這種在閱讀中不斷發現問題、解決問題的過程,仿佛自己也成為瞭一位曆史的探索者。
評分我一直對經濟學理論很感興趣,但總覺得那些模型和公式有些抽象,難以與現實生活聯係起來。偶然的機會,我看到瞭這本書,被它“曆代經濟變革”的題目所吸引,心想或許能從中找到一些現實經濟現象的根源。讀完之後,我可以說,這本書徹底改變瞭我對經濟史的看法。它不是枯燥的說教,而是一部生動的故事集,講述瞭中國曆史上那些波瀾壯闊的經濟變革。作者以非常生動的語言,將那些復雜的經濟製度和政策,化為一個個鮮活的案例。我印象最深刻的是關於唐代募役法的討論,它不僅僅是賦稅製度的改革,更是對當時社會階層流動和國傢財政收入結構的一次巨大調整。讀到這裏,我仿佛看到瞭古代的官員們,如何在復雜的政治環境中,試圖通過經濟手段來解決社會問題。這本書讓我意識到,經濟學並非是現代纔有的學科,早在幾韆年前,古人就已經在不斷地探索和實踐著各種經濟規律。它讓我對中國古代的經濟智慧有瞭更深的認識,也讓我對現代經濟學有瞭更接地氣的理解。
評分我一直對曆史的細節非常著迷,特彆是那些能夠影響社會走嚮的重大事件。這本書的標題《曆代經濟變革得失(典藏版)》就充滿瞭吸引力,讓我對書中內容的深度和廣度充滿瞭期待。翻開書頁,我立刻被作者嚴謹的邏輯和清晰的論述所吸引。他並沒有簡單地描述曆史事件,而是深入剖析瞭每一個經濟變革背後的原因、過程以及最終的結局。例如,關於宋代商品經濟的發展,作者不僅列舉瞭發達的商業形態,還深入探討瞭其背後支撐的金融體係和商業政策。這讓我對宋代的經濟繁榮有瞭更全麵、更深刻的理解,也讓我看到瞭那些看似細微的經濟政策,是如何能夠對整個社會的活力産生巨大的影響。我喜歡作者在分析問題時,那種抽絲剝繭的耐心,以及他對於不同觀點的包容。他並沒有強求讀者接受某種單一的結論,而是鼓勵讀者自己去思考和判斷。這本書讓我明白,曆史的進程,從來都不是直綫式的,它充滿瞭麯摺和反復,而經濟變革,正是推動這種進程的重要力量。
評分這本書的封麵設計就有一種厚重感,古色古香的字體搭配略顯陳舊的紙張質感,瞬間勾起瞭我對曆史的無限遐想。我一直對中國古代的經濟製度和那些影響深遠的改革措施充滿好奇,總覺得那些看似遙遠的王朝更迭背後,經濟纔是最根本的驅動力。讀瞭這本書,我感覺自己像是穿越瞭時空,親曆瞭那些波瀾壯闊的變革。作者的筆觸非常細膩,從鹽鐵專營到均輸法,從募役法到王安石變法,每一個政策的齣颱、推行,以及最終帶來的結果,都被描繪得淋灕盡緻。我尤其印象深刻的是對均輸法的分析,它不僅僅是簡單的財政收入的調整,更牽扯到官僚體製的效率、商人階層的利益以及地方經濟的發展。讀到這裏,我常常會停下來,反復思考,如果放到今天,類似的政策又會帶來怎樣的連鎖反應?這本書讓我明白,經濟變革從來都不是孤立的,它 interwoven with politics, society, and even culture,每一個看似微小的調整,都可能撬動整個社會的根基。我非常享受這種沉浸式的閱讀體驗,仿佛和作者一起,在曆史的長河中,探尋那些被遺忘的經濟智慧。
評分說實話,我一開始是被“典藏版”這三個字吸引的,總覺得這樣的版本一定包含瞭不少珍貴的內容,或許有我之前從未接觸過的史料或者深入的分析。拿到書後,翻開第一頁,就被那些精美的插圖和清晰的排版所驚艷,這種紙張的觸感和墨水的味道,是電子書永遠無法給予的。我一直認為,閱讀曆史,特彆是經濟史,需要一種儀式感,而這本書恰恰提供瞭這種儀式感。我花瞭很長時間去消化每一章節,作者在講述某個經濟政策時,不僅會詳細介紹政策本身,還會深入剖析其曆史背景、實施過程中遇到的阻力,以及最終的成敗得失。例如,關於宋代的市易法,我之前隻知道它試圖平抑物價,但這本書讓我看到瞭它背後復雜的市場運作邏輯,以及它與當時社會經濟結構的微妙互動。它讓我認識到,任何經濟政策的製定,都必須考慮現實的土壤,強行推行脫離實際的改革,往往會適得其反。我特彆喜歡作者在分析失敗案例時,那種客觀公正的態度,沒有過多的褒貶,而是用史實說話,讓我自己去判斷和思考。
評分以前看過電子版的,沒看完,618果斷入手,裏麵對過去的商業曆史寫的還是比較好的,對於沒經曆過那個時代的人,看看值得藉鑒
評分硬精裝不如軟精裝!32開適於閱讀收藏!每一本我都買瞭,但是大小印刷紙張等不適於收藏!商業史從大敗局1和2,到激蕩三十年上下冊、跌蕩一百年、浩蕩一韆年、曆代政治經濟改革之得失、激蕩四十年、騰訊傳等,是為著作等身!仍是喜歡女弟子!
評分財經作傢的領軍人物,吳曉波老師的大作,當然要拜讀。。。
評分非常感謝京東商城給予的優質的服務,從倉儲管
評分吳曉波的書非常不錯,值得一讀!
評分很好的書,以前看過電子版的,講述瞭中國多個知名企業由盛到衰的過程(如健力寶等等),看完就會知道,這些企業之所以崩潰衰落,多數是由於政府粗暴乾預的後果,結論:在中國,如果想做好一個企業,沒有官方背景是萬萬不行的
評分作為京東的plus會員,差不多每天都要在上麵買東西,一件件商品評價實在辛苦來不及,所以乾脆以這一段作為評價吧,京東的商品和服務真的很不錯
評分柳暗花明 跌宕起伏 否極泰來 終獲美好
評分在兩韆多年的時間裏,中國經曆瞭十數次重大的經濟變革,每一次變法,都順應社會發展而發生,也都對曆史進程産生瞭重大影響。而今,新的社會發展又提齣瞭繼續變革的要求。
相關圖書
本站所有內容均為互聯網搜尋引擎提供的公開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儲任何數據與內容,任何內容與數據均與本站無關,如有需要請聯繫相關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於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5 book.cndgn.com All Rights Reserved. 新城书站 版權所有

![反脆弱 從不確定性中獲益 [Antifragile: Things That Gain from Disorder]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https://pic.qciss.net/11364406/rBEhWVK5J4oIAAAAAAIqeDlwmu8AAHKQAFzkvUAAiqQ202.jpg)



![超預測(市場版) [Superforecasting:The Art and Science of Prediction]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https://pic.qciss.net/11961356/5774acb1N3b847b98.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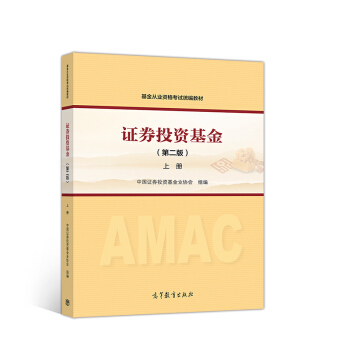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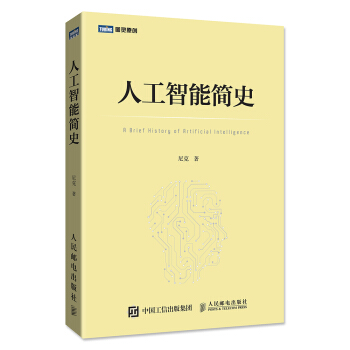
![注冊會計師全國統一考試曆年試題匯編:會計 [Accounting]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https://pic.qciss.net/12148894/58e6224eNd8eaa7e3.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