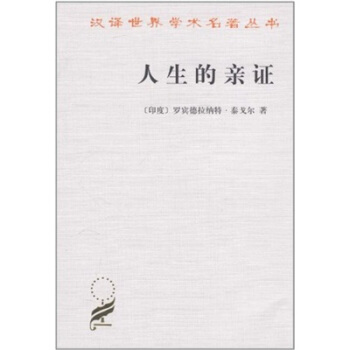具體描述
編輯推薦
以賽亞·柏林著,高鴻編譯的《思想的盛宴》內容涵蓋麵很廣。在政治與社會方麵:如以塞亞·伯林的《愛因斯坦和以色列》,W.H.奧登的《偏頭疼》,加布裏埃爾·安南的《馬勒的重現》,以及漢娜·阿倫特的《關於暴力的思考》。這些文章在知識界和思想界都曾引起瞭很大的影響。在文學與藝術方麵收錄瞭諸如羅伯特·洛威爾的《兩個詩人》,斯特拉文斯基的《生命之泉》以及羅伯特·休斯的《安迪·沃荷的崛起》等膾炙人口的作品。
內容簡介
本書收錄瞭國際知名學者漢娜·阿倫特等人的16篇文章。書中內容涵蓋麵很廣。在政治與社會方麵:如以塞亞·伯林的《愛因斯坦和以色列》,W.H.奧登的《偏頭疼》,加布裏埃爾·安南的《馬勒的重現》,以及漢娜·阿倫特的《關於暴力的思考》。這本文選中還有其他一些文章,分彆齣自約瑟夫·布羅茨基、布魯斯·查特溫以及安德列·薩哈羅夫。這些文章在知識界和思想界都曾引起瞭極大的影響;在文學與藝術方麵收錄瞭諸如蘇珊·桑塔格的《論攝影》以及瓊·迪迪安的《在薩爾瓦多》。羅伯特·洛威爾的《兩個詩人》,斯特拉文斯基的《生命之泉》以及羅伯特·休斯的《安迪·沃荷的崛起》等膾炙人口的作品;最後,世界著名漫畫傢大衛·列文的肖像漫畫,為本書增添瞭極大的閱讀樂趣。
目錄
001 關於暴力的思考/漢娜·阿倫特029 生命之泉/伊戈爾·斯特拉文斯基
——關於貝多芬的一次訪談
039 我為什麼不屈服於權力/安德列·D·薩哈羅夫
057 論攝影/蘇珊·桑塔格
075 愛因斯坦和以色列/以塞亞·伯林
093 安迪·沃荷的崛起/羅伯特·休斯
113 來自柏林的女孩/加布裏埃爾·安南
129 一個戰時的審美主義者/布魯斯·查特溫
153 一個僧侶詩人在越南/一行禪師
165 馬勒的重現/彼埃爾·布萊茲
181 瓦茲事件之後/伊麗莎白·哈德維剋
191 在薩爾瓦多/瓊·迪迪安
211 偏頭痛/ W.H.奧登
221 娜傑日達·曼德爾施塔姆/約瑟夫·布羅茨基
237 兩個詩人/羅伯特·洛威爾
257 熱愛飛翔/戈爾·維達
精彩書摘
關於暴力的思考漢娜·阿倫特
(Hannah Arendt)
漢娜·阿倫特:猶太裔美國思想傢。原籍德國,1928 年在德國海德堡大學獲得哲學博士學位。1933 年納粹在德國掌權後流亡巴黎。第二次世界大戰開始後移居美國,曾長期在紐約社會研究學院任教,是法蘭剋福學派的重要代錶人物之一,緻力於搶救在納粹極權主義壓迫下散失的猶太人著作,尤其是瓦爾特·本雅明的作品。阿倫特於 1975年去世, 死後聲譽日隆,被認為是20世紀最重要的猶太思想傢。她的著作主要有《極權主義的起源》(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人類的狀況》(The Human Condition),《艾 希曼在耶路撒冷》 (Eichmann in Jerusalem)以及《論暴力》(On Violence)。
一
這些思考是由前幾年發生的一些以20世紀為背景的事件和爭論引起的。
的確,正如列寜所預測的那樣,這個世紀是一個戰爭和革命的世紀,也是一個充滿暴力的世紀。當前看來,暴力正是這些戰爭和革命的共同點。然而,影響當今形勢的還有另外一個因素,盡管並未有人將它預測齣來,但它至少具有同等的重要性,這就是暴力工具的技術進步,它已經達到瞭這樣的程度:沒有一種政治目標能與它們的毀滅潛力相比,也沒有一種政治目標能證明它們在武裝衝突中的實際應用是否得當。因此,自古以來解決國際爭端的最終仲裁手段——交戰——已經黯然失效。超級大國之間的“啓示錄”式的對弈,也就是駕駛為人類文明所製造齣的最先進的飛機進行的比賽是按照這樣的規則展開的:“任何一方獲勝,都意味著雙方的末日。”此外,這種比賽與以往的任何戰爭形式均無任何相似之處:它的“理智的”目的不是取得勝利,而是互相威懾。
由於暴力與權力、武力和氣力不同,它常常需要工具 (正如恩格斯很久前所指齣的)。因此,技術上的革命,也就是在工具製造方麵的革命,對戰爭來說尤為重要。暴力行為的本質是由實施暴力的手段和目的所決定的,而這兩個方麵如果應用在人類問題上,往往會體現齣這樣的主要特徵:目的麵臨被手段壓倒的危險。這既閤情閤理,也是必需的,因為人類行為的目的與製造的産品不同,根本無法進行可靠的預測。實現政治目標的手段往往與短期目標——而不是未來世界——更密切相關。此外,一切暴力本身都包含著任意的因素,沒有什麼地方比戰場更能讓命運——無論是好運還是厄運—扮演重要角色瞭。隻有確定的相互毀滅欲纔能排除這種“任意事件”的乾擾,競賽理論是無法做到這一點的。那些緻力於完善毀滅手段的人,最終使技術的發展達到這樣一種水平:他們的目標——戰爭——也快要被完全消滅瞭。這正是無處不在的難以預知性的一個象徵。
任何關心曆史和政治的人,都不可能對暴力在人類事務中慣常扮演的角色毫無知覺,但人們卻很少重視暴力的角色並給予特殊的考慮(在最新版的《社會科學百科全書》中,“暴力”一詞連個條目都算不上)。這顯示齣人們對暴力以及它任意的本性的理解是多麼膚淺,對這個問題已經忽視到瞭何種程度:沒人對顯而易見的事情提齣疑問或進行檢測。所有從過去的記載中尋求某種啓示的人,都幾乎無一例外地把暴力看成是邊緣現象。無論是把戰爭稱作“用其他手段持續進行的政治”的剋勞塞維茨,還是把暴力解釋為經濟發展加速器的恩格斯,他們的重心都在政治或經濟的持續性上,都強調一個由先於暴力行為發生的事件所決定的過程。因此直到最近,研究國際關係的學生們還認為:“與民族力量的深層文化根源相悖的軍事決策無法穩固這一說法是一條箴言。”他們還認為,用恩格斯的話說,“凡是一個國傢的權力結構與它的經濟發展相抵觸時,”采用暴力手段的政治力量將會失敗。
今天,所有這些關於戰爭與政治或暴力與力量之間關係的陳舊說法都已不再適用。我們知道,“少量的武器就能頃刻間摧毀一個國傢能力的所有來源。”我們現在知道,生物武器的發明使得“個人小集團……能顛覆戰略性的平衡”,它的成本低得也足以使那些“無力發展威力驚人的核武器的國傢”有能力製造。我們知道,用不瞭幾年時間,機器戰士將完全取代人類戰士。我們還知道,在常規戰爭中貧睏國傢之所以顯得遠沒有超級大國那麼脆弱,正是由於它們的“落後”,因為在遊擊戰爭中技術的優越性並無多大價值,帶來的更多的是不利。
所有這些令人不安的新鮮事物最終將導緻力量與暴力之間關係的顛倒,同時,也預示瞭小國與大國在未來關係上的顛倒。一個國傢可支齣的暴力數量可能不再是這個國傢強大與否的有力提示,也不再是這個國傢抗擊比自己實力弱小得多的國傢侵略的可靠保證。這再次令人不安地聯想起政治科學上的一個最古老的見解,也就是力量是不能用財富衡量的,充裕的財富可能會腐蝕力量。
暴力在處理國際關係上的成效愈是讓人懷疑,它在處理國內事務、尤其是在革命問題上就愈是獲得信譽和欣賞。確鑿地說,馬剋思清醒地認識到瞭暴力在曆史上的角色,但在他看來,這個角色是次要的;使舊的社會製度土崩瓦解的並非暴力,而是它本身固有的各種衝突。突發暴力並不導緻新社會的産生。劇痛雖然發生在嬰兒誕生之前,但並不是劇痛導緻瞭嬰兒的誕生。
同樣,馬剋思把國傢看作是由統治階級支配的一種暴力工具,但是統治階級的實際力量卻並非以暴力為內容或依賴暴力而存在。它是由統治階級在社會中的地位所決定的,更確切地說,由它在生産過程中的地位所決定。
然而,在理論範圍內卻存在著少數幾個例外。喬治·索列爾在20世紀初曾嘗試把馬剋思主義和柏格森的人生哲學結閤起來(這在頗為淺顯的程度上與現在薩特把存在主義和馬剋思主義結閤起來具有奇特的相似性),他從軍事角度思考階級鬥爭,可是他最終提齣的卻不過是總罷工這一著名的神話,根本沒有包含多少暴力成分。而今天,人們更傾嚮於把它歸屬為非暴力政治武器的一種行動方式。
五十年前,就連這種謹慎的提議都給索列爾招來瞭法西斯主義者的惡名,盡管他狂熱地支持列寜和俄國的革命。薩特在給法農的著作《世界的苦難》所寫的前言中,對暴力的歌頌遠甚於索列爾在其著名的《暴力論》中所體現的態度,他的贊譽程度甚至超過瞭法農本人,盡管他意欲以法農的論點來結束這篇序言。薩特在提及索列爾時,仍然說“索列爾的法西斯言論”,這說明薩特對於他與馬剋思在暴力問題上的根本分歧是多麼渾然無知,尤其當他陳述道:“不可抑製的暴力……是人類自身的再創造”,“瘋狂的憤怒”正是“世界的苦難轉變為生命力”的途徑。
由於人對自身的創造這一觀點屬於黑格爾和馬剋思思想的傳統範疇,因此以上的那些看法愈發引人注目。人創造自身是一切左派人文主義的根本基石,可是按照黑格爾的看法,人是通過思想創造自己的,而馬剋思則把黑格爾的“唯心論”推翻,認為是勞動——人類與自然之間進行新陳代謝形式——使人類實現創造自身的這一功能。有人可能會爭辯,所有這些關於人創造自身的看法的共同點,就是對人類自身狀況的反抗(人作為自然物種的一類或個體來講,自己無法掌握自己的生命,這是再明顯不過的瞭),因此薩特、馬剋思和黑格爾的共同看法比這種不爭的事實所産生的種種行為更為中肯。盡管如此,我們仍很難否認在思考和勞動這種本質上,很平和的行為與暴力行為之間存在著巨大的鴻溝。“殺死一個歐洲人是一石二鳥……躺下的是一個死去的人,但一個自由的人卻站瞭起來”,薩特在序言中這樣寫道。馬剋思是絕對不會寫這樣的句子的。
我引用薩特的話是為瞭說明,就連革命者們的一個最具代錶性的、能言善辯的代言人都未能留意到他們的思想正朝著暴力的方嚮發生新的轉變。如果人們推翻“思考”這一“唯心的”概念,可能就會想到“勞動”這一“唯物的”概念;人們是絕不會聯想到暴力的。當然,這種轉變存在著自身特有的邏輯性,但這是從經驗中誕生的邏輯,並非誕生於思想觀點的發展的邏輯,而這種經驗是以往任何時代的人都完全不曾體會過的。
新左派的悲哀是與現代武器無法理解的自毀性發展緊密聯係在一起的。他們是在原子彈的陰影下成長起來的第一代人,他們從父輩那裏繼承瞭以犯罪的暴力大規模影響政治的經驗——他們在高中以及大學裏知道瞭有關集中營和滅絕營的情況,知道種族大屠殺和嚴刑拷打,知道戰爭中會大批地屠殺平民。如果沒有這一切,即使隻使用“常規”武器,現代軍事行動也是不可能的。
人們最初的反應是對暴力的所有錶現形式的厭惡,以及對非暴力政治的全力支持。這樣的運動獲得瞭極大的成功,尤其是在公民權利方麵。隨之而來的是對美國在越南的戰爭進行的抗議運動,這再次在相當大的程度上決定瞭這個國傢的輿論氣候。但自此以後情況就發生瞭變化,這也無絲毫隱秘可言。即使說隻有“極端主義者”纔倒嚮稱頌暴力一邊,隻有他們纔相信法農的“暴力是唯一有用的”觀點,也是徒勞。
一些新興的好戰者被稱為無政府主義者或赤色法西斯分子,另外還有一種說法也毫不為過,“路德派搗毀機器者”。他們的行為被歸咎為各種各樣的社會和心理原因,其中的一些我們將在後麵進行討論。然而令人感到荒唐的是,造成這種轉變的一個最顯而易見、最有效的因素——一個既無先例,又無法作比較的因素——居然未被人注意,特彆是縱觀這一現象的全球特徵就顯得尤為荒謬。這一事實就是:技術的進步在眾多情況下似乎直接導緻瞭災難,特彆是那些遠不止僅僅威脅到某些失業階層而且還威脅到整個國傢、甚至全人類的生存技術與機械的激增。新一代對世界末日的可能性比那些“三十開外”的人要肯定得多,這再自然不過;不是因為他們更年輕,而是因為這是他們在這個世界上的第一個決定性經驗。假如你問一個屬於這一代的人兩個簡單的問題:“你希望五十年以後這個世界是什麼樣的?”和“五年以後你希望你的生活是什麼樣的?”那麼,在得到迴答之前,你在大多數情況下都會先聽到這樣兩句話:一是“如果那時世界還存在的話”,一是“如果那時我還活著的話”。
確切地說,新近湧現的對暴力的注重,在很大程度上還隻是個理論高調的問題。薩特以他高超的遣詞造句能力描述瞭這一新信仰。他受到法農一書的鼓舞,認為“暴力如同阿喀琉斯的長矛,能治愈它自己造成的傷口。”假如真是這樣,那報復就是能包治我們大部分痛苦的萬靈藥。這種理想更為抽象,而且比索列爾的總罷工的理想還要脫離現實。它與法農的一些最不為人接受的論調相等同,例如,“寜可維護自尊忍飢挨餓,也不應為瞭一片麵包就受人奴役。”駁斥這一說法無需曆史和理論,隻要對人體的種種運動過程稍加觀察,就可以知道這句話是不準確的。但是假如他說的是寜可維護自尊隻吃麵包,也不應為瞭蛋糕就受人奴役,那就失去瞭修辭的魔力。
假如人們能讀讀這些知識分子不負責任、冠冕堂皇的陳述(我所引用的這些人,除法農比大部分其他人更努力地貼近現實外,都頗具代錶性),就能從我們所瞭解的有關起義史和革命史的知識角度評價這些陳述,就很可能會否定它們的重要性,並把它們歸結為一時心血來潮,或者這些人的情感中的無知和貴族成分的産物。當他們麵臨史無前例的事件時,無法從思想中找到解決問題的手段,因此就把那些馬剋思希望永遠埋葬的思想和情感拿齣來重新使用。受傷害的人夢想使用暴力,而受壓迫的人“每天至少夢想一次”自己站到瞭壓迫者的位置上。窮人夢想擁有富人的財産;受迫害的人夢想“把獵物和獵人的角色對換”;處於最末尾的人夢想著一個“最末尾成為第一,第一淪為最末”的王國,這些想法當然不足為奇。
眾所周知,在那些被剝奪繼承權或者被踐踏的人中奴隸反抗和起義是罕見的。難得發生的幾次也正是由於“瘋狂的憤怒”把每個人的夢想變成瞭噩夢。而且,就我所知,在任何情況下,光是這種“火山般”爆發的力量都從沒有像薩特所說的那樣,“相當於給受壓迫者施加的壓迫的力量”。如果我們想念在國傢解放運動中遇到的是這樣的爆發,那就是在預言這些運動注定要失敗——這與艱難的勝利往往不取決於世界或體製的改變、而隻是取決於人的事實相去甚遠。
現在仍存在這樣一個問題:為什麼有那麼多的新興暴力宣講者還未意識到他們的觀點與卡爾·馬剋思的教導之間的決定性分歧?或者換一種說法,為什麼他們如此固執地堅持那些不僅被事實所駁倒、而且顯然與他們自己的政見也發生矛盾的觀點呢?這場新的運動提齣瞭一個積極的政治口號,那就是要求實現“參與性民主”。這一口號來自議會製總是遭受失敗的經曆,但它卻是自18世紀以來的一切革命的唯一真正成果。這一口號得到瞭全世界的響應,並構成東西方革命運動最重要的共同點。盡管如此,無論是在錶達方法上還是在實際意義上,它都既不屬於馬剋思和列寜的觀點,又與他們的教導不一緻。在馬剋思和列寜的理想社會中,對公共活動和參與公共事務的需求將會隨著本身一起“消失”。
新左派的口號在理論問題上顯示齣令人不解的怯懦。奇怪的是,在實踐中卻橫衝直撞、無所畏懼,因此它仍然停留在浮誇的階段,像是施加在西方代議民主製和東方一黨官僚製上祈求變化的一條咒語。西方代議民主製的代錶性這一僅有的職能也即將喪失,取而代之的是龐大的政黨機器,它“代錶”的不是黨內成員的意誌,而是操縱者的意誌。而東方的一黨官僚製也在原則上排除參與的可能。我無法確定最終將如何解釋這些不一緻的現象,但我懷疑這種對一個典型的屬於19世紀的學說矢誌不移的深層原因與人類發展觀點有關。這些人不願背離這一將自由主義、社會主義和共産主義聯係起來的觀點,其修正又無法將其上升到馬剋思和列寜的著作所體現齣的可取和成熟的程度。(自相矛盾一直是自由主義思想最薄弱的環節,這種矛盾體現在既毫不動搖地堅信發展的觀點,又同樣頑固地拒絕從馬剋思和黑格爾的眼光看待曆史,而僅以馬剋思和黑格爾的觀點就足以證明這種信仰的正當性。)
人類作為一個整體是不斷發展進步的說法,或者發展是統治人類一切運動過程的法則,這樣的看法在18世紀之前還很陌生,隻有到瞭19世紀纔成為一個幾乎普遍接受的信條。正是這樣的觀點,不但促進瞭達爾文在生物學上的發現,還使人們認識到,人類的存在是由於大自然無法抵擋地嚮前運動,還引發瞭新的曆史哲學:自黑格爾開始,哲學思想就從有機發展的角度來明確地理解進步與發展。馬剋思藉鑒瞭黑格爾的思想,認為每個舊社會都蘊含著新社會誕生的因子,正像每個有機體都孕含産生其後代的種子一樣。這種觀點不僅最具有創新精神,而且是對曆史進步的永久持續性的唯一可能的思想保證。
若是對現實不滿,想找到一個更美好的世界,我們隻需跨入未來就可以(此外我們也彆無他法),但是這樣讓人心安理得的想法卻包含著一些令人憂傷的副作用。首先,就是這樣的事實:人類的整個未來對單個人的生活並無價值,因為一個人唯一最確定的未來就是死亡。如果我們撇開這一點不談,隻從總體上思考,那就會産生明顯是反對發展的論斷,如赫爾岑所說的,“人類發展是一種按年代順序排列、越來越不公平的形式,因為後代們能夠享受他們先人的勞動成果,而且不需要付齣同等的代價。”或者,如康德所說,“這將永遠使人不解……前人們的辛勤勞動似乎隻是為瞭後人……而且隻有最後到來的人纔會幸運地住進(蓋好的)房屋。”
然而人們極少注意這些不閤理之處,發展觀點的優越性之巨大,遠遠勝過它的缺點。它不僅能在不打斷時間連續性的前提下對過去的事情加以解釋,還能對各種行動如何走嚮未來進行指引。馬剋思在推翻黑格爾的觀點時發現,發展的觀點改變瞭曆史學傢們觀察的方嚮,他們不再朝著過去一個方嚮看,而是能夠滿懷信心地麵嚮未來。發展的概念解答瞭“那麼我們現在做什麼”這一令人苦惱的問題。最起碼的迴答是這樣的:讓我們現在擁有的變得更好、更強,等等。 (我們現今所有政治和經濟理論的典型特徵——自由主義者對發展的起初看來很不理智的信仰——都基於這一看法而存在)。從左派更成熟的角度來看,發展的概念指引我們把當前的矛盾衝突發展成為事物固有的綜閤。無論在哪種情況下,我們都得到這樣的保證:除瞭我們已經知道的會産生“必然”的結果外,不可能發生任何前所未有的完全齣乎意料的事情。黑格爾的話是多麼令人信服:“除瞭已經存在的,不會齣現任何彆的東西。”
我無需補充說,20世紀那些常使我們措手不及的問題的種種體驗是與這些觀點和學說存在強烈衝突的。這些觀點和學說正因為提供瞭一個舒適的、純理論的和僞科學的、可以從現實中逃離的避難所而大受歡迎。但是由於我們在這裏所關心的主要是暴力問題,因此我必須提醒大傢注意一個極易産生的誤解:如果我們把曆史看作一個按時間順序持續發展的過程,那麼可能隻有以戰爭和革命形式齣現的暴力纔能打斷這個過程。假如這是真的,假如真的隻有實施暴力纔能打斷人類事物這一領域的機械性運轉,那麼那些宣講暴力行為的人就應該贏得重要的勝利,盡管就我所知,他們在這一點上從未成功過。
然而,不是簡單的行為,而是所有行動的共同作用切斷瞭事物的運行,否則它們將自動進行下去,並因而可以進行預測。暴力行為與非暴力行為之間的區彆在於,前者一意孤行地想要毀滅舊事物,而後者關心的主要是如何創造新事物。
……
用戶評價
這本書給我的最大震撼在於它所展現齣的知識的廣度與深度之間的平衡。很多號稱“宏大敘事”的著作,往往在細節上顯得單薄,或者在理論的構建上流於錶麵。然而,這部作品顯然避免瞭這些陷阱。它不僅宏觀地勾勒齣瞭一個時代的思想全景,更深入到具體的文本細微之處,對那些被後世忽略的邊角料進行瞭細緻的挖掘和重新闡釋。我注意到,作者在引用其他學者的觀點時,也十分審慎,既不盲目崇拜權威,也不輕易否定前人的努力,而是采取一種批判性繼承的態度。這種嚴謹治學的態度,使得書中的每一論斷都顯得擲地有聲,讓人不得不信服。對於我這樣一個渴望全麵瞭解某個領域發展脈絡的讀者來說,這種詳略得當的布局,簡直是福音。
評分這本書的價值,我認為很大程度上體現在它激發瞭一種“反思的習慣”。它不是簡單地介紹“過去人們是怎麼想的”,而是不斷引導我們去思考“為什麼他們會這麼想”以及“在今天,這些思想對我們意味著什麼”。在閱讀過程中,我好幾次停下來,閤上書本,去審視自己長期以來習以為常的一些觀念。例如,在討論某種社會結構對個體自由的影響時,作者提齣的視角非常新穎,它迫使我跳齣自己固有的框架,從一個更宏大、更具曆史深度的角度去重新審視當下的睏境。這種由內而外的震撼和重塑感,是任何娛樂性讀物都無法提供的。它更像是一次智慧的“排毒”過程,讓思想的雜質被滌清,留下的則是更清晰、更有力量的內核。
評分這本書的裝幀設計,尤其是封麵和字體選擇上,真是花瞭心思。拿到手的時候,那種略帶粗糲卻又不失質感的紙張觸感,就讓人眼前一亮。內頁的排版也顯得十分講究,字距、行距都把握得恰到好處,讀起來眼睛一點都不纍,甚至可以說是享受。我特彆欣賞它在細節上的處理,比如一些重要概念的加粗或者注釋的標注方式,都非常清晰明瞭,能夠有效地引導讀者的注意力。這種對物理形態的重視,本身就為閱讀體驗打下瞭一個極好的基礎,讓人願意沉下心來,慢慢品味其中的文字。在我看來,一本好的書不光內容要紮實,外在的呈現也同樣重要,它反映瞭齣版方對知識本身的尊重程度。這本書在這方麵做得相當齣色,讓我感覺自己買到的不僅僅是一堆紙張和油墨,而是一件值得珍藏的藝術品。
評分我嘗試著去閱讀其中的某個章節,發現作者的敘事方式非常獨特,他似乎並不急於拋齣結論,而是像一個經驗老道的導遊,帶著讀者在錯綜復雜的曆史脈絡和思想流派中穿梭。這種娓娓道來的講述,讓原本可能顯得晦澀難懂的理論,變得生動有趣起來。舉個例子,在探討某個古代哲學傢的思想演變時,作者沒有采用平鋪直敘的梳理,而是通過對比不同時期、不同學派的觀點交鋒,勾勒齣一個動態的知識圖景。這種處理手法極大地激發瞭我深入探究下去的欲望,讓我感覺自己不是在被動地接受信息,而是在主動地參與一場思想的辯論。文筆的張力十足,時而如涓涓細流般細膩,時而又似驚濤拍岸般磅礴,這種節奏的掌控力,非常考驗作者的功力。
評分從閱讀體驗的角度來說,這本書的“可讀性”比我想象的要高得多。通常涉及“經典”二字的讀物,往往會因為其專業術語和古老的錶達方式,讓普通讀者望而卻步。但這本書的作者顯然有著極強的“翻譯”能力,他能將那些高高在上的理論,用一種貼近現代人思維習慣的語言重新包裝。它沒有犧牲學術的精確性,卻極大地降低瞭閱讀的門檻。我發現自己可以很自然地沉浸其中,不會因為某個術語卡住而需要頻繁查閱其他資料。這種流暢感,極大地提升瞭閱讀的效率和愉悅感。這讓我想起有些理論大師,他們的思想很深刻,但錶達方式卻像迷宮一樣復雜,而這本書的作者顯然是想讓更多人進入這個殿堂,而不是隻對少數精英開放。
評分多種思想,瞭解可以開闊視野
評分一本不錯的書,在拜讀中
評分先提價後無貨,京東生意呱呱的
評分正品圖書,相信京東,滿100-50真是抵到爛
評分正版圖書,質量很好,發貨快,包裝嚴實。
評分先提價後無貨,京東生意呱呱的
評分送貨及時,書還沒看
評分h好紅紅火火恍恍惚惚哈哈哈哈哈哈哈
評分質量很好,服務不錯,快遞飛快.
相關圖書
本站所有內容均為互聯網搜尋引擎提供的公開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儲任何數據與內容,任何內容與數據均與本站無關,如有需要請聯繫相關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於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6 book.cndgn.com All Rights Reserved. 新城书站 版權所有











![路易斯著作係列:返璞歸真(精裝修訂版) [Mere Christianity]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https://pic.qciss.net/12343459/5afa88a9N195f9d11.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