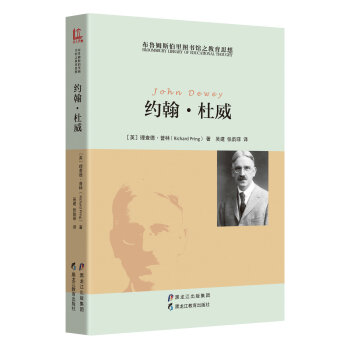

具体描述
编辑推荐
★ 约翰·杜威从哲学转向教育并且在理论与实践结合的基础上始终探索现代教育,构建了实用教育思想体系。杜威在其漫长生涯中,一直坚持着“实践哲学”的理念,对教育提出批评及改革建议,既有教育的哲思,也作日常思索。他不甘心教育沦为“别的目的的附属物”;
★ 约翰·杜威对社会变迁有着敏锐的判断,其坚持着“实践哲学”的理念,让“虚无”更加清晰,促进中西方教育观念互相借鉴;
★ 理查德·普林以批判的眼光从不同的角度重新解读杜威的核心理念,不仅追忆教育的历史,也指导现在的教育发展;
★ 亚里士多德、柏拉图、杰罗姆·布鲁纳、杜威、福柯、保罗·弗莱雷、欧文、皮亚杰、卢梭以及维果斯基,单从名字看就构成了西方教育发展的历史轨迹。从希腊罗马时代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到18世纪的卢梭,19世纪的皮亚杰、杜威,再到20世纪的福柯与布鲁纳,每一位教育家的理念观点都堪称西方教育发展的里程碑!
★【布鲁姆斯伯里图书馆之教育思想】全系精彩图书:
海报:
内容简介
《约翰·杜威》深入地介绍了世界知名教育家约翰·杜威的教育理念和主要观点。对人类文明、思想教育的发展等问题,杜威以他深邃的思考、尽可能浅显的文笔,为我们做了一次兼顾总结与展望的说明……认知、建构、发展区间、阶段施教、批判性意识、提问式教育等名词,构成了西方教育家的核心观点,在近当代西方教育领域起着节点性的作用。中国的现代教育借鉴了西方教育的体系与理念,从近代开始,中国就提倡西学,包括如今的教育体系都是早由西方引进的,从这个意义上而言,这些教育鼻祖的理念仍具有广泛的现实意义。
《约翰·杜威》称杜威“被公认为美国当代哲学界在世的代表人物”。如此盛誉,部分归功于实用主义意义理论,据称该理论解决了诸多哲学及教育学难题。但人们对杜威的褒贬主要针对其教育思想。在美国,那些主张儿童中心教育的人,视杜威为美国教育的救星。但另有一帮人认为杜威妨碍了传统教育,说他“比希特勒还糟糕”。这种控诉在英国也不乏呼应之声。本书讲述的是杜威的教育思想,时时提醒着人们,其教育思想背后乃实用主义意义观这一哲学基础。作者理查德·普林力图证明,杜威是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教育哲学思想家。
《约翰·杜威》一书隶属于《布鲁姆斯伯里图书馆之教育思想》系列丛书,本丛书含有10个分册,每个分册深入介绍一位世界知名教育家的教育理念和主要观点,从新时代的客观诉求出发来重新阐释这些教育家的主张,也以新的视角重新衡量了这些教育家的思想。每一位教育家都可谓是他们所处时代的标杆,所处地域的教育学鼻祖,本书系以批判的眼光从不同的角度重新解读这些教育家的核心理念,不仅追忆了教育的历史,也指导了现在的教育发展。
作者简介
理查德·普林,英国牛津大学格林坦普顿学院教育系荣誉退休教授,目前在英国温彻斯特大学教书。作品有:《教育的哲学》(2004)、《大众教育》(2009)、《教育循证实践》(2005)以及《大众中等教育的生与亡》(2013)
内页插图
精彩书评
这本书的重要性实难低估。理查德·普林用清晰、细致但不失全面的分析框架,阐明了杜威思想的性质及其复杂结构。普林认同杜威的诸种主张,尤其他对探索性质的阐释和所重视的兴趣,让广大师生有机会深入了解一位时常看似晦涩难懂的思想家。
——休·绍克特,美国乔治梅森大学教育学教授
目录
丛书主编序言序
前言
第一部分 思想传记
第一章 杜威其人及其生平、著作与遗产
第二部 分约翰·杜威教育思想评述
第二章 教育的目的
第三章 经验、理解、认识与探索
第四章 儿童中心教育
第五章 课程的逻辑与心理维度
第六章 社群与个人:民主与伦理
第三部分 哲学基础
第七章 实用主义:意义、真理与价值
第四部分 属于我们时代的教育哲学家
第八章 当下的问题与杜威的“回答”
参考文献
索引
精彩书摘
杜威其人及其生平、著作与遗产
芝加哥大学与纽约哥伦比亚大学
在纽约曼哈顿122号街矗立着闻名遐迩的哥伦比亚大学。约翰·杜威在这所高等学府任哲学教授长达26个年头。但对他而言,思考哲学和思考教育之间是一脉相通的。他对“经验”的哲学分析构成了他教育理念的核心要素,他认为教育的宗旨乃“成长”,这也可追溯到他关于意义和价值的实用主义理论。因此,在他授课的大厅里,不光有教育专业学生,也挤满了未来的哲学家。他退休后,影响也毫未衰减。他仍笔耕不辍,四处奔走讲学,直到1952年去世。在哥大期间,他写了《哲学与教育》(Democracy and Education,1916),书中系统地讲述了其教育哲学观。
来哥大任教之前,杜威在芝加哥大学任哲学系、心理学系与教育系主任。杜威是在1894年,即他35岁时上任的。杜威的哲学思想影响十分深远,哲学家威廉·詹姆斯说:
芝加哥有一个思想流派!未来25年,该派思想会被记载为芝加哥流派。
一些大学有很多思想,但没有形成流派,还有一些大学有很多流派,但没有思想。芝加哥大学凭借其鸿篇巨制《十年出版物》(Decennial Publications),展示了真正的思想和真正的流派。约翰·杜威教授以及至少10个他的门徒,集体向世界宣布了一个世界观。他们虽然人数不少,却众口一谈—理论联系实践,简洁明了、叙事宏大、主旨明确;尽管还有很多地方需要细致完善,但足以获得新哲学体系的殊号了。
上文提到的出版物,包括杜威的关于逻辑理论的一篇文章以及乔治·赫伯特·米德的一篇关于“心灵的定义”(the definition of the psychical)的文章。
但在1904年到哥大前这10年,杜威的哲学思想和教育思想是并驾齐驱、共同演变的。如我之前所说,这两者之间是密不可分的。他在芝加哥大学期间写成的教育思想著作《学校与社会》(School and Society)与《儿童与课程》(Child and Curriculum),体现了《我们是如何思考的》(1910年出版于他离开芝加哥大学后,但主要是在芝大时写的)中明示的一些原则。这是一本教师的哲学指导书。某种意义上而言,哲学和教育似乎互不相关。当我们思考我们从事教育活动时到底在做什么时,我们其实是在思考教育的目的,思考指导实践的价值观,思考所传播的知识和经验的本质,这些其实都是哲学思考。再者,此种思考并不能脱离实践,而是在理解实践,旨在改善实践。因此,思考必须要基于教育实践。在芝加哥大学,杜威和妻子一起创办了一所大学初等学校,亲任校长。这所学校属于大学一部分,与大学的教师培养活动相结合。
学术影响
我们研读影响杜威在芝加哥期间及其余生教育思考的信念之前,首先应说说他在芝加哥大学任职前的生平以及影响他本人成长的重要哲学思潮。
杜威1859年出生于佛蒙特州伯灵顿。16岁上佛蒙特大学,在那里他读到了达尔文的《物种的起源》(1859年出版),参与了由该书引起的辩论。进化论对杜威哲学以及教育学思想产生了持久的影响。在哲学意义上,其解答了心身二元论,杜威认为从若干方面来看,心身二元是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传统的错误源头。人类只是更高级的生物有机体,有内在的目标,因此会有目的性地适应环境,而环境也包括人际交往和文化的社会环境。
1879年杜威从佛蒙特大学毕业,头3年先是在几所学校任教,但并不成功,随后便进入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读哲学研究生。他的一位同学便是查尔斯·桑德斯·皮尔斯,皮尔斯被公认为“实用主义”(pragmatism)之“父”。不过,皮尔斯后来将其更名为“实效主义”(pragmaticism)。这个名字太难听了,杜威和威廉·詹姆斯等人不屑窃用。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杜威还受到了黑格尔唯心论的影响,部分通过其学长乔治·莫里斯(George Morris),部分通过他后来认识的牛津大学唯心论者F.H.布拉德利(F.H.Bradley)和T.H.格林(T.H.Green)。黑格尔的哲学“要求融合统一,这无疑是一种强烈的渴望,也只有知识化的题材内容才能满足这种渴望。”
如果要简短草率地总结下这对杜威成长的影响,我们可以说杜威“对统一的需求”使得他有了以下信念:第一,所有经验都有内在的联系;第二,心灵能发现这些内在联系;第三,“观察的心灵”和“被观察的世界”之间的二元对立会消解。生命应被视为一种“有机体”,但人类并非纯生物意义上存在;人类有机体中固有的思想和使命感通过经验得以实现。
1884年,杜威跟随莫里斯来到密歇根大学,最终成为这所大学的哲学系主任。在这里,杜威阅读了T.H.格林的著作,他的唯心主义倾向演化为社会思考[1889年发表于《安多弗评论》(Andover Review)的《托马斯·希尔·格林的哲学》(The philosophy of Thomas Hill Green)一文等]。他的社会思考有两个与后来形成的教育理念密切相关。一、哲学在理解与解决公共与社会生活中扮演核心作用;二、自由对于人最大程度自我实现具有伦理价值。这里说的“最大程度自我实现”是发生在社会语境中的一个个人最大利益即等于大家最大利益的集体。
在他于芝加哥大学任职前,我们已经可以看到一些让威廉·詹姆斯宣称“芝加哥有思想流派”的要素了:每个“人类有机体”通过适应社会环境成长;该适应是有目的性的,每个个体的人都在其经验中寻找意义;该适应通过与其他人互动产生,而其他人也在寻找其经验的意义;互动的语境即个体构成的集体,集体因个体之间的互动而生,也进而影响个体之间的互动;这种有目的性的适应的最终目的(伦理意义上的终点)即能够适应这些互动经验,并从中获益;最后,其中的社会议程便是去解决集体生活的问题。那么,教育便可被用以促成这种成长和适应。
五个核心信念
杜威创建大学初等学校背后有一套教育哲学,其根基为5个信条。这些信念影响了杜威的思想50多个年头,自始至终变化甚少。杜威在1897年任职芝加哥大学后不久写了《我的教育信条》(MyPedagogicCreed),其中陈述了这些信条。这是杜威对传统教育方式的回应。他认为传统的教育方式:
脱离了学生在家庭与社区习得的经验;
脱离了学生获取经验的实践与手工活动;
忽视了激励年轻人学习的兴趣;
把知识看作纯粹的象征和形式:以课本形式组织,粘贴在一起,与经验或者现有的理解方式毫无联系;
通过外在权威维护纪律,而非通过年轻人的积极参与。
杜威在实验学校(见下文)中提供的解决方案即是对这种传统教育理念的回应。
第一,学校应是家庭和社区的延伸,将对日常生活至关重要或至少十分有用的理解的获取置于更加宏大的体系。很多实际知识其实是在家庭或社区习得的,而学校的目的应是深化这一理解,促使年轻人去反思这一理解,提升其价值,给他们一些能够回馈家庭和社区的东西,并加深他们对二者的理解。
第二,作为家庭和社区经验的延伸,学校应该重视手工与实践活动,因为手工与实践活动是家庭与集体生活不可或缺、有意义的部分。正是通过手工与实践活动,如木工与纺织,人们才能理解日常生存与生活的基础。而这是那些擅长就人类处境发表宏论的人所常常忽视的。
第三,年轻人的兴趣应该受到足够重视,而不是要去管束,使其符合教师的目标,让他们做他们实际上不感兴趣的事情。而兴趣本身是需要教育培养的,因为兴趣是学习的动力。
第四,学校课程至多只能代表我们所继承的知识体系,但也只是有用的知识体系,其目的是帮助我们在世界上更智慧地行事。其价值在于其有用性,是人们解决问题所需的资源,但很少有问题会恰好落入各个科目的逻辑范畴。
第五,如果年轻人的兴趣得到重视,教师主动帮助其发展兴趣(即给年轻人更多机会与自己更智慧、更成熟地交流),那么年轻人将愿意追随兴趣,根本无需外部约束。
因此,学校不应仅仅被视为社会的延伸,其本身就应被当作一个社群,学生应是该社群的积极成员。行为的约束不应源自外部强加的制裁,而是内化的社群生活规范。
所以,杜威兴办实验学校面向的是普通青年学生,他们好奇、有兴趣,但其好奇心和兴趣却被各种根本不顾及其学习兴趣的学习模式所削弱。而学校应该充分考虑探索的过程,鼓励学生去追逐兴趣,确保其获得教师的专业知识以及通过教师这个渠道传授的文化资源。而在良好的学校集体中,个体在追逐自身兴趣的同时也会考虑集体的需求。
杜威的教育方法本质上是实验性的。这一点不难想到,因为杜威自己的哲学立场后来即被冠名“实验主义”。理念必须要通过实践加以检验。因此,创建学校—后来被称为“实验学校”,来检验教育理念就至关重要了。1901年,杜威调至芝大教育研究所,开始开展教师培训项目。而当时研究所已有一所“培训学校”。同一家机构有两所学校,难免会有混乱。杜威1904年前往哥伦比亚大学后,实验学校便无以为继,但其理念却得以长存。
本书随后章节中会介绍这些理念。这些理念与当时的教育实践格格不入,当时的基础教育基本上只起着信息传递的作用。杜威视之为契机,积极研究问题、寻找出路、尝试“假说”、将社群当作资源、思考问题的解决方案。这些问题部分是社会性的,即如何与追求不同兴趣的人和谐相处,虽然这些兴趣常常是交相作用的。某种程度上,受教育便意味着与学校集体的其他个体和谐共处,从他人身上学习观念和经验。学校就是个小社会。
杜威于1904年离开芝加哥大学转任哥伦比亚大学。但毫无疑问,杜威在校那10年在芝加哥大学留下了深深的烙印。芝加哥大学也成了世界主要教育研究机构之一,与教育实践紧密结合。菲利普·杰克逊(Philip Jackson)便是一例,他的《课堂中的生活》(Life in Classrooms,1968)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教师。但曾经的教育学流派不复存在了。为了证明自己学术正确,该流派学者不再与课堂保持亲密的日常接触,开始写作发表研究成果。虽附属于社会学流派,但其发表的研究成果似乎并不符合社会学流派的标准。在各学术流派的眼中,该流派变得无足轻重,在各大高校眼中,又没有学术价值,举目无亲,最终消亡。如果这个流派当初听从了“老伙计”约翰·杜威就好了。杜威认为理论如果与实践脱节,则理论便会扭曲,实践亦会贫乏。(英国如今的大学科研评估机构是否应该把此话记在心上?)
杜威在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度过了他漫长学术生涯的剩余时间。他最重要的教育学著作《民主与教育》发表于1916年,即他在哥大任教期间。这本书很长,文风较为生涩,但每章最后皆有小结解惑。和其他既冗长又难懂的书一样,这本书也招来了误读。20多年后的1938年,杜威写了一本简短的著作《经验与教育》(Experence and Education),解释了他的作品不应简单冠之以什么“主义”,尤其是“进步主义”。事实上,教育哲学家不应站在任何一方(“传统主义者”或是“进步主义者”)的立场上,也不应该在二者中间寻求什么中间路线,而是应该引入“一套新的概念,引入新的实践模式。”
正是这个理念与做法让杜威时至今日仍不过时。教育话语中所反映出来的种种教育实践冲突都可归咎于杜威激烈反对的二元论:学术与职业、理论与实践、学习与休闲、学校与社会,还有基于传统科目的学习与探索式学习或基于兴趣的学习。或许正如杜威所说,我们需要找到“一套新的概念,引入新的实践模式。”
上面说的“一套新的概念”便包含在杜威于芝加哥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从教30年间出版的一系列哲学论著中,主要关乎教育话题。为了写作本书,我尤其参照了下列最直接反映其教育思想的文章与书籍:
《我的教育信条》(My pedagogic creed,1897),《学校杂志》
《学校与社会》,1899年举行的三场讲座,于1900年发表,1915年修订,分别为《学校与社会进步》(School and social progress),《学校与儿童生活》(The school and the life of the child)以及《教育中的浪费》(Waste in education)
《儿童与课程设置》(The Child and the Curriculum,1902)
《我们如何思考》(How We Think,1910)
《民主与教育》(Democracy and Education,1916)
《经验与教育》(Experience and Education,1983)
至于更加具体的哲学思考,我参考了下列著作,因为这三本著作为杜威的教育思考提供了哲学基础:
《哲学的重建》(Reconstruction in Philosophy,1920)
《经验与自然》(Experience and Nature,1925)
《逻辑:探索的理论》(Logic:the Theory of Inquiry,1938)
本书并未详述约翰·杜威对其他主要思想家(哲学家、社会学家和教育家)的广泛影响,不过,如果有人去挖掘这个话题,肯定既有趣又有价值。不过我想,杜威对乔治·赫伯特·米德的影响十分重大,而米德对后来的教育社会家也影响深远。米德是杜威的同事,米德分析社会关系的主要方法—符号互动论(symbolic interactionism),便源自皮尔斯和杜威的实用主义传统。这又进而影响了北美和英国几代社会学家和教育研究者。杜威的间接影响少有人提及,即便是“行动研究”支持者也闭口不谈。行动研究广受欢迎,似乎成了“学校改良”的解决方案。但大卫·布里奇斯在他近作中指出,勒温(Lewin)及其门徒的行动研究其实源自杜威的实用主义的意义理论。因此,从事行动研究的人应对实用主义意义理论加以承认,尽管该理论有这样那样的问题。
教育的目的
定义之问题
在《民主与教育》一书中,杜威“给教育作了技术上的定义”,即“重建或重组经验,充实经验的意义,并提高人们指导未来经验的能力。”书中对教育是什么,给了诸多其他说法,但皆是这个核心定义的延伸或阐释。不过,在我们解释这个定义之前,或许应该说说到底什么是定义。杜威到底在做什么?定义一个单词即阐明其意义和在语言中的使用。
因此给单词下定义并不是给出其他可选项,而是展示该单词是如何使用的,使用的规则为何以及在某特定话语形式中的位置。因此,有些单词有多重意义,因为在不同语境中有不同的使用方式。我所说的不同,并非指单词意义的模棱两可(如‘plane’这个词既可以指飞机,也可以指刨子),而是不同用法之间有重合。一个单词可能会有很多不同的用法,便有了不同的定义,虽然同属于一个广泛的“相似家族”。
“教育”便是这么一个词语。不同的人对其有不同的用法(对于什么样的人算是受过教育的人这一概念,不同的人也会有不同的看法),但不同的应用会有一些共同特征。其中一个共同特征便是以某种方式提升知识,而且只指人,不指狗或马。为什么呢?因为只有人,而非动物才有能力对各种情形获得概念性掌握,以便合理应对,而不仅是作行为性反应。这种学习会导向进一步学习,通过获取新知识、理解力与技能以增强能力。当然,有人会不加区分,讨论动物的教育,而非仅仅动物的训练。这种观点是缩小动物和人的区别,把通常赋予人的品质赋予动物。教育意味着学识的增长,而非行为的改变。
再者,我们口中所说的“教育”常常也包含着评价的意义。人们受到教育便会进步,更有能力做应当做的事情。人们会变得丰富。因此,当我们说某人是“受过教育的人”,实际是一种褒扬。因为获得了某些能力,丰富、提升了素养。
因此,人们还可以说,教育这个词既有描述性意义,也有评价性意义。就描述性意义而言,教育指的是实际发生的学习,就评价性意义而言,教育指这种好的、可以提升素养的学习。即便就描述性意义而言,也很难完全抹去教育这个词的评价性内涵。
学校被视为教育机构,并非仅仅因为学校是帮助年轻人学习的正式场所,也因为人们认为学校学习本身具有价值,可增益思考,是值得追求的目标。如果人们认为学校在灌输某种信条,遏制思考,那么人们就会说,尽管可以学习到一些东西,但年轻人在这里并非在受教育。
因此,一些组织式学习从描述意义上或可称之为教育,但从评价意义上讲,或许不应被视为教育。
教育概念比较
我在上文对教育这个字眼做了基本的分析,即这个词在描述意义上和评价意义上是如何使用的。我没有做更细节的分析。当本书介绍部分提及的“哲学革命”开始禁锢教育领域的思考时,教育哲学家们便对该词做了详细的剖析。皮特斯(Peters,1966)依据用法设定了标准,并依此认为,若一个活动导向知识与理解力的拓展,且该知识并非狭隘知识,而是提供了更广的“认知视角”,且该知识被认为是有价值的,那么该活动则可被称为“教育”。分析哲学家们虽设置了这些标准,但声称他们只不过分析了这个概念在我们日常语言中的使用—世界在日常语言中的“映射”。哲学是二阶行为。这种分析并非告诉我们什么值得教、如何教。
这一哲学阵营对杜威的批评有两重。第一、就什么值得教、什么值得学,杜威却言语明确。他僭越了哲学家的职责。第二、杜威认为有价值的—即对经验的改观或重建、自我实现、成长,都逃脱不了哲学分析的手术刀。“成长”本身不能成为终极目的,其价值存在于“成长”引向的最终产品。
杜威若在世,他会指出,他的批评者是在打着“二阶行为”的幌子,实则有他们自己的教育理念—即什么是受过教育的人,而这其实也无法从该词汇本身的用法中得出。所谓受过教育的人,指某人获取了思考、探索和推理的特定知识。在英国,R.S.皮特斯的同事保罗·赫斯特(Paul Hirst)对此做了十分有效的阐释。他于1965年发表了《自由教育与知识的本质》(Liberal education and the nature of knowledge)一文,此文乃女王督察局制定学校课程时所涵盖的八大经验领域的哲学基础。女王督察局的这一举措影响深远。在美国薛夫勒和施瓦布(Schwab,1964)也有类似的重要著作。这些知识形式可以按照核心概念、检验模式与探索方法加以分析。因此,有人从所谓的概念分析角度,提出了实质性课程建议,和杜威的观点截然不同。
杜威重点关注的不是学习的具体成果,即不同的知识与逻辑结构。这些区分由哲学家界定,是教学的主要内容。杜威关注的是生命有机体的“成长过程”。该成长来自于环境的互动。这个环境既是物质的,也是社会的,所以并非纯粹生物概念上的成长。正如杜威在《儿童与课程》(CC;见本书结尾处杜威作品目录缩写)中说:
教育过程中的根本要素是一个未成熟的、欠发展的人;而一些社会目的、意义和价值观已然具化在成人成熟了的经验中。教育过程便是这些因素的相互作用。教育理论的本质便是探索如何使这些因素彻底、自由地互动。
这种成长或“教育过程”,即“未成熟的、欠发展的人”与环境之间的互动,这里的环境包括成人的社会环境。成长并非简单的增长(如河流变大变宽),而是对旧我的改变。受教育者对世界的理解被重新概念化了,并非增加了新的想法。习惯得以改变,技能得以提升,对世界有了新的理解,能够更有效地适应这个世界,个人经验得以进一步改变。如果要论及教育过程的最终目标,则应该是更好的成长和更佳的适应能力,而非某特定、界定明确的(由大学、考试委员会或政府界定)知识的获取。但事实上,这种转型变化是持续不断的,没有终点。教育“在每个阶段都有成长的目标”。成长没有终点,一直到死。
对杜威而言,一些经验是非教育性质的,甚至是错误的教育,因为其阻碍了通向进一步经验的途径或抑制了思维,即使属于教育体系的一部分,即使在内容和意图上均在向年轻人传授不同形式的知识。这就是为什么杜威自始至终都在批判他所谓的“传统教育”。虽是系统地传授知识,但却未能改造年轻人思考、感知、体验和信仰的方式(这是评价意义上的教育)。比如,学数学时死记硬背乘法表在描述意义上可谓教育(这算作学校学习内容的一部分),但从评价意义上来说却是错误的教育方式,因为(肯定会有人对此持有异议)死记硬背阻碍了理解。
那对杜威而言,什么经验才能算教育,什么算不得教育呢?
首先,正如上文所言,如果不能带来更丰富的经验,甚至起到阻碍作用,过于死板,令人恐惧,或一味教化,令思维固化,那就算不得真正的教育。如果学生为了文学课考试要死记硬背,可能因此生厌,再不想读文学了。就算考试得了高分,其中的经验却是错误的教育。
第二,经验的教育内涵或价值在于独特人性的发展,即其经验世界的能力(人乃世界的一部分,但却在某种程度上独立于世界)。经验会改变这一能力,使其更好地面对新经验—预期、计划。创造经验,以生成更多经验和能力来与更广阔的世界打交道。因此,经验便是对世界的概念化、内在化,这反而又影响新的经验以及处理新经验的能力。新经验既改变已有经验,又受之影响,因此改变一个人预期及处理未来经验的能力。
举个简单的例子,这就如同一个小孩被狗咬过,这会改变这个孩子以前对狗的经验。“狗”的意义变得复杂了,不再是友好的、可以搂搂抱抱的动物了,而变成一种很凶、很危险的形象。这一经验的改造改变了这个孩子未来的行为,使其能更好地面对未来的经验,更好地预判危险、应对新的经验。过于幼小的孩子因经验过于狭隘而无法生存下去。早期教育便是获得、改造经验,使幼孩得以存活,对环境拥有一定的掌握。童年如果缺乏经验,那么孩子便不能很好地预期和处理未来经验,这或许会危及生存。
前言/序言
丛书主编 序言
教育有时呈现为一种基本的实践活动,关乎教与学、关乎课程设置、关乎学校开展的诸项活动。教育旨在运用某些方法达到某些目标,这些目标和方法通常早已拟定好,交由教师执行,而教师的职责便是热情、忠实地贯彻这些目标和方法。既然有如此清晰的目标,那么理论的价值何在?
近年来,不同国家的政客和决策者们旗帜鲜明地否认教育理论的价值或必要性。原因何在?20世纪90年代,英国教育大臣曾说过一句惊人的言论,从中可以看出端倪:“对儿童如何学习、发展或感知,具有任何意见,都是一种颠覆之举。”这句话言简意赅地点出了理论的困境:理论颠覆、挑战、破坏了教育实践赖以生存的基本观念。
于是,教育理论家成了思想王国里的惹是生非者。他们对现状构成威胁,引导我们去质疑关于教育实践的常识观念。但这恰恰是他们应当做的,因为他们关于学校和教育的论述虽然简单,却蕴含着无数可争论的概念。这些概念在不同的用法中,反映了完全不同的教育目标、价值和行为。
《布鲁姆斯伯里图书馆之教育思想》(Bloomsbury Library of Educational Thought)这套丛书便是在含蓄地宣告:理论和构建理论对教育而言至关重要。从古希腊到当代学者,将这些最重要、最有趣的教育思想家的思想汇集起来,为一代学生和教育从业者提供既易于获得又具有权威性的资源,是本丛书的宏伟任务。本丛书各册均由该领域学识广博的领军人物撰写,之所以选择这些学者,既是因为他们学术成就卓越,也是因为他们擅长以通俗易懂的语言阐述复杂的思想,以飨广大读者。
对于本丛书呈现的重要思想家的名单,可能始终难以令所有人满意。有些人也许会质疑某些思想家被列入名单,有些人也许会对其他思想家没有入选而心存异议。这种情况不可避免。我们也决不认为《布鲁姆斯伯里图书馆之教育思想》提出的思想家名单是不容置疑的。不可争辩的是,这些思想家对教育都阐述过令人叹服的思想,而本丛书将其集结成册。因此,对教育研究者而言,本丛书不失为信息与灵感的强大源泉。
理查德·贝利,伦敦,罗汉普顿大学
序
约翰·杜威(John Dewey)很可能是20世纪最知名、最广为承认也最受诟病(其实有失公正)的教育哲学家了。他因“儿童中心教育”思想而备受关注。他的很多哲学和教育著作论及教育之宗旨以及他对儿童兴趣的关注、经验对教育的重要性、探索是知识和理解的主要源泉和集体对个体成长的重要性。杜威的著述确实促发了不少战前“进步主义教育运动”实践(新教育协会及其创办的《新时代》杂志便是一例,杜威是该杂志撰稿人之一)。该运动所倡导的理念于20世纪60年代被《普劳顿报告》(Plowden Report)奉为圭臬,该报告调查的是英国小学教育及其影响。到了1970年,英国的英语教师和校长们被请到美国,为美国教师传授教学经验,有趣的是,这些经验却源自于美国哲学家的教育著作。
当然,正如理查德·普林(Richard Pring)在这部清晰而有趣的研究中指出,不少人自称热爱杜威的思想,但却少有人真正读过这位哲学家精心写就、言辞谨慎、时而生涩的哲学著作。杜威的“门徒”们不久便矫枉过正,而杜威本人也不得不对其加以纠正,甚至要与其撇清关系。英、美两国的右翼政治家后来开始妖魔化杜威[杜威的《民主与教育》(Democracy and Education)被列为20世纪最危险的著作之一,仅次于希特勒的《我的奋斗》(Mein Kampf)和马克思的《资本论》(Das Kapital)]。这实际上源自两重无知:一重是对杜威真正言论的无知,一重则是对英、美两国学校情况变迁,或者是并未真正发生变化的无知。本书对杜威哲学和教育哲学观点做了深刻的解读,读者因而更能明白追随者们为何如此敬仰杜威的著述以及对于我们教育体系的败笔,杜威是否担有责任,或担有多大责任。
但吊诡的是,在20世纪后二三十年代,杜威的学说虽被驱逐出狭义的教育圈子,却以其他形式抛头露面。“儿童中心学习说”或许遭到了学校体系的摒弃,但“学生中心学习”以及“学习者中心学习”等观点在成人和继续教育中得以保留,沿用至今。“项目学习法”或许在小学教育中失去了地位,但“基于项目或问题的学习”,一般围绕真实生活中的问题,却成为职业教育的准则。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或许已经过时,但科尔布(Kolb)的经验学习周期理论几乎在每个“培训人员”的培训手册中都要提及。科尔布的理论说到底就是简化和系统化了的实用主义。行动研究在全世界广受教育工作者们热情拥护,很多教育主管部门也乐于支持,其实是建立在知识及其发展的实用观之上的。在学习理论、课程话语以及正在快速发展的定性研究领域,杜威的实用主义以及他共事多年的同事乔治·赫伯特·米德(George Herbert Mead)的社会心理学理论,联袂奉上的概念框架最受推崇。时至今日,在美、英两国,政府资助机构对于教育研究的态度也是实用主义的。即研究应该告诉他们“什么管用”。不过,杜威若仍在世,很可能会愤怒地指责这是对他实用主义认识论的滥用。
如今《民主与教育》已出版近一个世纪,杜威学说仍然具有广泛的指导意义,这一点,我想是毋庸置疑的。但杜威哲学和教育论著所受到的待遇,无论公正与否,都表明,如果我们想真正从杜威的真知灼见中获益,那么必须要努力去理解其理念的哲学根基。理查德·普林是一位卓越的哲学家和教育家,长期研究杜威著述,有足够的资质引领我们阅读杜威的哲学和教育思想。此书是一本优秀的介绍之作,清晰地展示了约翰·杜威确实是“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哲学家”。
大卫·布里奇斯,剑桥大学圣埃德蒙学院冯·许格尔研究所和东英吉利大学教授
前言
当年在伦敦大学学院哲学系当本科生时,我常在图书馆里与约翰·杜威的一排著作相对而坐。我对这个人物有些好奇。一个人怎么写了这么多书,世人却读之甚少?我学了三年哲学,却从未在课堂里听人提起他的名字,也从未听说有人借阅或读过这些数量众多却布满灰尘的文献。他唯一出名的地方似乎只是因为他的著作被归为一个诡异的类别(当然有失公允)。
这在某种程度上有些吊诡。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在1946年初版的《西方哲学史》(History of Western Philosophy)中称杜威“被公认为美国当代哲学界在世的代表人物。”罗伯特·威斯布鲁克(Robert Westbrook)在《约翰·杜威与美国民主》(John Dewey and American Democracy)中称杜威“会成为美国现代史上最重要的哲学家,无论全世界的人如何褒贬他。”杜威—尤其是(在罗素看来)他对“真理”概念的论述—虽然遭到了误解,但仍有着巨大的影响力,在美国也不例外。
“美国当代哲学界在世的代表人物”这一殊荣,部分归功于他的“实用主义意义理论”,解决了很多使人困惑的哲学命题。杜威的“实用主义”对乔治·赫伯特·米德的社会心理学产生了重要影响。米德与杜威先在密歇根大学共事,后又是芝加哥大学同事。米德的理论阐明了个人身份是如何通过社会互动(符号互动)形成的,该理论迄今还在影响人种学范式下的教育研究。杜威影响了米德,也受到了米德的影响。尽管实用主义哲学影响深远,罗素给予“实用主义之父”,C.S.皮尔斯(C.S.Peirce)的待遇更是奇怪,书中提到他时只有寥寥两行(在讲杜威的那一章),在同一章中还简短提及了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
或许正因为此,杜威在英国才未获得他在美国受到的重视。我读过皮尔斯的著作,因为他被列入了课程大纲。但实用主义却从未进入哲学中心传统。据罗素(1946b,p.774)看来,这或是因为,人们无法接受“基本的逻辑概念和知识理论乃‘探索’,而非‘真理’”这一说法。
再往后来,由于阿兰·瑞安(Alan Ryan)《约翰·杜威和美国自由主义高潮》(John Dewey and the High Tide of American Liberalism,1995)一书的出版,英国学界对杜威产生了一些兴趣。这本书将杜威的哲学、政治学和教育学理念置于其生平及美国的政治社会生活中来理解。这确实是合理的,正如瑞安所言,杜威的论述是对这一社会语境的体现、阐释和互动,目标瞄向“智慧行动”。
杜威的哲学论述虽未受重视,他的教育论述却极具影响,尤其在美国“进步主义行动”中影响巨大。杜威哥伦比亚大学的同事W.H.基尔帕特里克(W.H.Kilpatrick)于1918年出版《项目教学法》(The Project Method)一书,此书将杜威的教育理念具体化为课程大纲,用实用、跨学科的项目来激励学习者,让其接触完成项目所需的不同门类的知识。
但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衡量理念到底好不好的一个标准,是看其会带来什么样的结果。美国于20世纪70年代日益面临日本及其他国家的经济挑战,陷入了经济困境,这是美国教育系统,尤其是“进步主义教育家”们不得不面临的问题,其中领军人物便是杜威(据批评者们而言)。正如奈尔·诺丁斯(Nell Noddings)在《教育哲学》(Philosophy of Education)中所说:
那些希望学生更多参与计划和活动的人赞誉他为美国教育的拯救者,但也有人说他“比希特勒还恶劣”,谴责他用认识论和道德相对主义影响了学校教育,还企图用社会化代替真正的教育。(Noddings,2005)
拉里·库班(Larry Cuban,2004)在《黑板与底线:为什么学校不能办成企业》(The Blackboard and the Bottom Line:Why Schools Can’t Be Businesses)中,提及教育正在倒退回一种运用高风险评价机制的商业模式,这正是杜威倡导教育理念的对立面。
但把“进步主义教育”的所谓恶劣后果归咎于杜威是不妥的。杜威本人对“进步主义教育”的很多做法也持彻头彻尾的批判态度。但给杜威头上安上这桩罪名也反映了教育思想很容易变成口号。正如薛夫勒(Israel Scheffler)在《教育的语言》(The Language of Education)中所说:
约翰·杜威对教育所产生的影响是一则富有教益案例。他的论述系统,谨慎而得当,很快便被转化成美国教育中新进步主义倾向的响亮口号。杜威自己也批判对他理念的诸种不当运用。(1960,p.37)
战后英国教育发展的批评者们,也把“以儿童为中心”这一奇谈怪论归咎于杜威的影响。所谓进步主义学说的论述常常提及杜威。布莱恩·西蒙(Brian Simon)称杜威学说是“1930年‘小学’革命”的影响之一,也成为1967年普劳顿报告书背后的“正统意识形态”(Simon,1991,p.362)。1989年我到牛津大学,晚餐时坐在基思·约瑟夫爵士(Lord Keith Joseph)身边,他曾在玛格丽特·撒切尔首相内阁任教育大臣。他责备我应该为我国学校的诸多问题负责,因为是我把约翰·杜威学说介绍给了教师们。之后,即便是哲学家、记者和政客们都开始系统地攻击作为教育家的杜威。比如,奥黑尔(O’Hear)教授就说“我们教育质量的下滑,大抵要怪罪约翰·杜威学说倡导的平等主义(1991,p.28)。”
第一,至少在英国,很少有人仔细研读杜威的教育学说,正如很少有人仔细研读他的哲学著作。英、美两国的教育哲学家们虽然常常提及杜威(皮特斯在他1981年写的《教育家论集》(Essays on Educators)中做了评述,笔锋虽有同情,但批判得也算彻底。1970年,伦敦教育学院教育研究所一个研究小组花了数周时间研读了杜威的《民主与教育》。美国教育研究协会也有一个活跃的教育研究小组,专门致力于杜威批判研究。但这些学术研究凤毛麟角,很难把教师群体变得激进起来。所以,很难看出杜威学说如何改变了人心,或影响了实际的教育发展,除非是因为他的哲学在培训教师的教育学院广为传播。
第二,达林(Darling,1994)在《儿童中心教育观及其批判者》(Child-Centred Education and Its Critics)一书中,详细描述了学界对杜威观念的批判,批判有两点:其一,“哲学革命”[吉尔伯特·赖尔(Gilbert Ryle)于1956年出版著作的标题]开始主导教育哲学,而此时在英国教育研究正欲成为显学。其二,以色列·薛夫勒等哲学家正在革新北美的教育观念,薛夫勒的著作《教育的语言》(The Language of Education)影响广泛。哲学家们不再认为哲学的目标是回答诸如教育目标是什么、教师该如何教学等实质性问题,而是就教育到底指什么(及其目标)、教学是何概念等,提供一些二阶逻辑分析。因此,“新哲学”激烈地批判以哲学之名开出的教育药方。R.D.阿香博(R.D.Archambault)(教育哲学革新的北美倡导者之一)说“需要清理马厩”,“教育哲学家们没有认识到或利用好近些年的哲学研究成果”(1965,p.8)。
哲学阐释问题,但并不提供解决方案。伦敦教育学院的“革新者们”,在理查德·皮特斯的带领下,尤其关注儿童中心观的说法。其中自然包括杜威以及各种儿童中心教育论中所谓教育目标乃“成长”和“自我实现”之类的说法。正是这一说法,引得迪尔登(Dearden)(《小学教育的哲学》原文,1968,pp.37ff.)和皮特斯(见《教育与对教师的教育》原文,1977)等分析哲学家们大举批判。杜威作为哲学家想要改变实践。但在革新后的教育哲学思潮来看,这是不可接受的。当然,除非实践的改变源自清晰的理论思考。这一新正统思潮与杜威以及他所倡导教育理念格格不入。我们会在第三章再来谈杜威的教育理念。
第三,巧合的是,在哲学家们一边批判杜威的同时,英国保守派政府及美国联邦政府对学校的标准与效用也日趋失望。而当时儿童中心教育观正在遭受批判,自然便被视为祸根。因此,北美和英国都在批判所谓的进步主义教育,呼吁更加正式的教学方法,并对知识学习进行更加系统的评价。而杜威则常被视为罪魁祸首。
不过,那些认真研读杜威众多著作的人,会发现其观点不易理解,而考虑到如今的教育体系对于那些学习意愿差的学生无能为力,我们又会发现杜威的观点很有道理。另外,他的哲学观点渗透了他的教育理念,如果不能理解他的实用主义哲学,便很难接受他的教育理念。比如,不少人可能会同意罗素的评判,认为杜威用“探索”替换“真理”,作为知识理论体系中的基本概念。杜威的哲学观念和教育思想彼此交错,如果不能接受杜威的哲学立场,则很难接受他的教育观念,不管其看起来多么有道理。
本书共分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介绍杜威的生平与著述,第二部分分析塑造杜威教育思想与实践的关键理念。本书难免会触及哲学,但我会在第三部分才对实用主义哲学(杜威称之为“经验主义”或“工具主义”)做系统的阐释。最后,在第四部分,我会将两者合一,看看是否能起到什么挽救之用。
杜威哲学观点的性质让人有信心对其加以评论阐释。作为解释,我先来预告下,我随后会如何评述实用主义哲学。实用主义哲学是关于意义的哲学。单词、句子或文本的意义在于其所起到的实际效果。当然,这样的实际效果一定受文本所塑造,必受该文本中的语言词汇所约束。再者,杜威笔下的文字对于我的意义则在于,其改造了我看待、思考杜威的视角,尽管这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我研读杜威文本的语境和兴趣。常常很难区分,什么是杜威文本本身的意义,什么是对于我而言的意义。因此,我在讲述杜威时,其实是在(我也有权这么做)讲述杜威对于我的意义(效果)。我的讲述进而会“重构”他人的“重构”,因此变成了杜威言论意义的一部分。
想要理解杜威的教育思想,必须先理解其教育思想所基于的关键概念。我挑选了七个概念。通过这些概念,或许能理解他丰富的论述。不过,可能会有不少人并不认同我所列的关键概念,也因此不认同我对杜威的解读。
教育目标(儿童的兴趣、约束和成长);
经验(对经验进行反思);
探索(以及理解和真理指什么);
儿童中心论;
课程的知识和题材;
社群(以及个人在其中的位置);
学校教育(及其与社会的关系)。
我在1987年写过一篇文章。文中,我说杜威很可能是“技术与职业教育计划(TVEI)的守护神”(Pring,1989)。英国就业部人力服务委员会于1983年发起该计划,强调实践和经验的学习,质疑学术与职业学习的分野,质疑“虚假的”二元主义,并坚持学习内容要和社会更紧密联系。该计划在全国范围内受到欢迎,即便如此,1988年英国实施全国统一课程时,该计划也夭折了。但计划作者和创造者从未读过杜威的作品,我想杜威也会在这项计划的实践行动中看到自己理念的影子。而那些在实施全国统一课程时拒绝该计划的人,也会拒绝他的理念。
因此,本书真正的主题关乎教育实践所基于的理念—即教育目的意识形态之争,因为教育目的嵌在教育实践之中。为了说清道明这些理念,我写作此书时会围绕杜威,但无疑也会时常游离于他的文本之外。但我对此并不担心,杜威如果在世,也不会介意。因为杜威说,言说或文本的意义在于其所产生的效果。杜威的论著帮我“重构”了我对教育实践的理解。我也希望我的阐释也会改造他的文本,因为理解永远处于动态之中。杜威说,理解永远没有终点。
用户评价
从整体结构来看,这本书的编排布局展现了一种宏大的历史视野。它不仅仅是在阐述一套孤立的教育学说,而是将其置于一个更广阔的社会变迁和哲学思潮的背景之下进行考察。你会发现,作者的思考是如何回应他所处时代的困境与希望的,这使得全书具有一种强烈的时代共鸣感。每一次从一个具体议题跳跃到更宏观的文化批判时,我都感到一阵心神震动,仿佛是站在一个高处俯瞰整个教育思想的演进脉络。这种结构上的疏密有致,大处着眼,小处着手的处理方式,让这本书超越了一般的专业论著,具备了文化史著作的厚重感和价值。它不是教你“怎么做”,而是引导你思考“为什么是这样”,这种根本性的追问,才是思想的真正价值所在。
评分这本书的装帧设计简直是一场视觉的盛宴,那种厚重的、带着微微泛黄的纸张触感,立刻就将你拉入了一种沉静的、需要慢下来的阅读氛围中。封面那种古典的、略带浮雕感的字体排版,透露出一种对知识的敬畏感,让人忍不住想去探究其中蕴含的深邃学问。我常常在想,好的书籍不仅仅是内容的载体,它本身也是一件艺术品。当你把它摆在书架上时,它不仅仅是一个标题,更像是一个宣言,昭示着主人对思想深度的追求。每一次翻开它,指尖拂过书页边缘时,都能感受到一种仪式感,仿佛自己正准备进入一个由文字构建的、充满历史回响的殿堂。这种精心打磨的实体感,在如今这个充斥着电子屏幕的时代,显得尤为珍贵和令人安心。它不是那种可以随便翻阅、快速消费的读物,而是需要你投入时间,甚至需要一盏台灯、一杯热饮来配合,才能真正领会其精髓的“老朋友”。
评分我花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才大致读完这套书,过程比我想象的要曲折得多,但收获是实实在在的。它的行文风格极为严谨,充满了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学术论辩的特有腔调,那种层层递进、步步为营的逻辑推演,对习惯了碎片化信息的现代读者来说,无疑是一个不小的挑战。我好几次因为某个哲学概念的阐释过于晦涩而不得不停下来,翻阅大量的补充注释和背景资料,才能勉强跟上作者的思路。然而,正是这种“难啃”,才造就了它思想的坚实骨架。它不像当代流行理论那样迎合大众口味,而是要求读者主动地去构建理解的桥梁。每一次成功攻克一个难关,那种智力上的满足感,是看再多轻松读物也无法替代的。这本书更像是一次智力上的马拉松,考验的不仅是你的阅读速度,更是你的专注力和对复杂概念的解析能力。
评分不得不提的是,这本书在语言运用上的那种老派的精确性,简直是一种艺术。作者似乎对每一个词语的选择都经过了千锤百炼,力求达到一种无可指摘的清晰度。即便是处理那些抽象的、难以言喻的哲学思辨,他也能找到一种既能保持深度又不至于陷入无谓玄虚的表达方式。这种文字的力量在于它的穿透性,它不是那种华丽的辞藻堆砌,而是直指核心的精准打击。我尤其欣赏其中那些长句的结构美感,虽然初读时需要放慢语速,但一旦掌握了其内在的从句关系和逻辑层次,那种完整的思想洪流带来的冲击感是惊人的。对于那些对语言文字本身抱有敬畏之心的读者来说,这本书简直就是一场关于如何进行高质量思考和表达的示范课。
评分这本书给我最大的启发在于它对“实践”与“理论”之间关系的深刻洞察。很多时候,我们习惯将教育视为一种纯粹的知识的灌输或技能的训练,但这本书却不断提醒我们,真正的教育必须扎根于真实的生活经验之中。它似乎在挑战那种高高在上的、脱离了泥土的教育构想,强调学习不应该是一种被动的接受,而是一种主动的、与环境互动的创造过程。读到那些关于儿童如何通过“做中学”来建构世界的章节时,我仿佛被拉回到了自己的童年,重新审视了那些看似简单的游戏和探索,原来背后蕴含着如此强大的学习动力。这种将教育视为生命整体有机发展一部分的视角,极大地拓宽了我对“什么是教育”的定义边界,让我开始重新审视自己日常工作和生活中的许多惯性做法。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内容均为互联网搜索引擎提供的公开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储任何数据与内容,任何内容与数据均与本站无关,如有需要请联系相关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于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6 book.cndgn.com All Rights Reserved. 新城书站 版权所有






![晚清英语教科书发展研究 [The Development of English Textbooks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qciss.net/12058907/58ef41bdNb8d046e6.jpg)









![汉语同位同指组合研究 [On Co-Referential Apposition In Chinese]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qciss.net/12065141/5901b5d9N0e1ac562.jpg)



![人类学学刊(第2辑) [Journal of Anthropological Studies Vol.2]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qciss.net/12068357/59157fe5N224f7f8d.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