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具体描述
编辑推荐
作者周作人生前亲自编定,学者止庵穷数年之力精心作校,增补从未出版作品,为市场上全面的周氏文集。鲁迅评价,周作人的散文为中国。
胡适说,大陆可看的唯有周作人的作品。
内容简介
《周作人自编集:过去的工作》收入周作人在抗战胜利前后(一九四五年四月至十二月)所作文章十五篇。文章延续四十年代以来风格,一类仍作“闲适”之谈,写景,状物,评文,娓娓道来,如《关于竹枝词》《石板路》《东昌坊故事》;一类则继续“正经”探讨思想,追根溯源,掷地有声,如《凡人的信仰》《过去的工作》《两个鬼的文章》,在周作人的写作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分量;而怀念陈独秀、钱玄同、刘半农三位旧友,则通过摘抄、注释他们的尺牍,勾陈昔日交往酬和情状,“流水斜阳”之情尽现笔端,为怀人之作开辟了一条新路。作者简介
周作人(1885-1967),现代作家、翻译家,原名櫆寿,字星杓,后改名奎绶,自号起孟、启明(又作岂明)、知堂等,笔名仲密、药堂等。浙江绍兴人。青年时代留学日本,与兄树人(鲁迅)一起翻译介绍外国文学。五四时期任教北京大学,在《新青年》《语丝》《新潮》等多种刊物上发表文章,论文《人的文学》《平民的文学》,诗《小河》等均为新文学运动振聋发聩之作。首倡美文,《喝茶》《北京的茶食》等创立了中国美文的典范。在外国文学艺术的翻译介绍方面,尤其钟情希腊日本文学,贡献巨大。著有自编集《艺术与生活》《自己的园地》《雨天的书》等三十多种,译有《日本狂言选》《伊索寓言》等。精彩书评
周作人的散文为中国。—— 鲁迅
大陆可看的唯有周作人的作品。
—— 胡适
周作人先生的读书笔记不可及,有其淹博的学识,就没有他那通达的见地,而胸中通达的,又缺少学识;两者难得如周先生那样兼全的。
—— 朱自清
周先生读书,没有半点冬烘气,懂得体会得,如故交相叙,一句是一句,两句是两句,切切实实地说一番。
—— 曹聚仁
目录
关于竹枝词谈胡俗
关于红姑娘
石板路
再谈禽言
关于遗令
读书疑
东昌坊故事
焦里堂的笔记
凡人的信仰
饼斋的尺牍
实庵的尺牍
曲庵的尺牍
过去的工作
两个鬼的文章
精彩书摘
关于竹枝词七八年前曾经为友人题所编《燕都风土丛书》,写过一篇小文,上半云:
“不佞从小喜杂览。所喜读的品类本杂,而地志小书为其重要的一类,古迹名胜固复不恶,若所最爱者乃是风俗物产这一方面也。中国地大物博,书籍浩如烟海,如欲贪多实实力有不及,故其间亦只能以曾游或所知者为限,其他则偶尔涉及而已。不佞生于会稽,曾寓居杭州南京,今住北平,已有二十余年,则最久矣。在杭州时才十三四岁,得读砚云甲编中之《陶庵梦忆》,心甚喜之,为后来搜集乡人著作之始基,惜以乏力至今所收不能多耳。尔后见啸园刊本《清嘉录》,记吴事而可通于两浙,先后搜得其异本四种,《藤阴杂记》,《天咫偶闻》及《燕京岁时记》,皆言北京事者,常在案头,若《帝京景物略》则文章尤佳妙,唯恨南京一略终不可得见,辜负余六年浪迹白门,无物作纪念也。”
去年冬天写《十堂笔谈》,其九是谈风土志的,其中有云:
“中国旧书史部地理类中有杂记一门,性质很是特别,本是史的资料,却很多文艺的兴味,虽是小品居多,一直为文人所爱读,流传比较的广。这一类书里所记的大都是一地方的古迹传说,物产风俗,其事既多新奇可喜,假如文章写得好一点,自然更引人入胜,而且因为说的是一地方的事,内容固易于有统一,更令读者感觉对于乡土之爱,这是读大部分的地理书时所没有的。这些地理杂记,我觉得他好,就是材料好,意思好,或是文章好的,大约有这几类,其一是记一地方的风物的,单就古代来说,晋之《南方草木状》,唐之《北户录》与《岭表录异》,向来为艺林所珍重。中国博物之学不发达,农医二家门户各别,士人知道一点自然物差不多只靠这些,此外还有《诗经》《楚辞》的名物笺注而已。其二是关于前代的,因为在变乱之后,举目有河山之异,著者大都是逸民遗老,追怀昔年风景,自不禁感慨系之,其文章既含有感情分子,追逐过去的梦影,鄙事俚语不忍舍弃,其人又率有豪气,大胆的抒写,所以读者自然为之感动倾倒。宋之《梦华》《梦粱》二录,明之《如梦录》与《梦忆》,都是此例。其三是讲本地的,这本来可以同第一类并算,不过有这一点差别,前者所记多系异地,后者则对于故乡或是第二故乡的留恋,重在怀旧而非知新。我们在北京的人便就北京来说吧,燕云十六州的往事,若能存有纪录,未始不是有意思的事,可惜没有什么留遗,所以我们的话只好从明朝说起。明末的《帝京景物略》是我所喜欢的一部书,即使后来有《日下旧闻》等,博雅精密可以超过,却总是参考的类书,没有《景物略》的那种文艺价值。清末的书有《天咫偶闻》与《燕京岁时记》,也都是好的,民国以后出板的有枝巢子的《旧京琐记》,我也觉得很好,只可惜写得太少罢了。”
上边两节虽是偶尔写成,可是把我对于地志杂记或风土志的爱好之意说的颇为明白,不过以前所说以散文为主,现在拿来应用于韵文方面,反正道理也是一样。韵文的风土志一类的东西,这是些什么呢?《两都》《二京》,以至《会稽三赋》,也都是的,但我所说的不是这种大著,实在只是所谓竹枝词之类而已。说起竹枝的历史,大家总追踪到刘禹锡那里去,其实这当然古已有之,关于人的汉有刘子政的《列女传赞》,关于物的晋有郭景纯的《山海经图赞》,不过以七言绝句的体裁,而名为竹枝者,以刘禹锡作为最早,这也是事实。案《刘梦得文集》卷九,竹枝词九首又二首,收在乐府类内,观小引所言,盖本是拟作俗歌,取其含思宛转,有淇濮之艳,大概可以说是子夜歌之近体诗化吧。由此可知以七言四句,歌咏风俗人情,稍涉俳调者,乃是竹枝正宗,但是后来引申,咏史事,咏名胜,咏方物,这样便又与古时的图赞相接连,而且篇章加多,往往凑成百篇的整数,虽然风趣较前稍差,可是种类繁富,在地志与诗集中间也自占有一部分地位了。这种书最初多称百咏,现存最早的著作要算是《郴江百咏》,著者阮阅,即是编《诗话总龟》的人,此书作于宋宣和中,已在今八百年前矣。元明之间所作亦不甚少,唯清初朱竹垞的《鸳鸯湖棹歌》出,乃更有名,竹枝词之盛行于世,实始于此。竹垞作《棹歌》在康熙甲寅,谭舟石和之,至乾隆甲午,陆和仲张芑堂又各和作百首,蔚成巨册,前后相去正一百年,可谓盛事。此后作者甚多,纪晓岚的《乌鲁木齐杂诗》与蔡铁耕的《吴歈百绝》,可以算是特别有意味之作。百咏之类当初大抵只是简单的诗集,偶尔有点小注或解题,后来注渐增多,不但说明本事,为读诗所必需,而且差不多成为当然必具的一部分,写得好的时候往往如读风土小记,或者比原诗还要觉得有趣味。厉惕斋著《真州竹枝词》四百首,前有小引一卷,叙述一年间风俗行事,有一万二千余言,又黄公度著《日本杂事诗》,王锡祺抄录其注为《日本杂事》一卷,刊入《小方壶斋丛钞》中,即是一例。这一类的诗集,名称或为百咏,或为杂咏,体裁多是七言绝句,亦或有用
五言绝句,或五言七言律诗者,其性质则专咏古迹名胜,风俗方物,或年中行事,亦或有歌咏岁时之一段落如新年,社会之一方面如市肆或乐户情事者,但总而言之可合称之为风土诗,其以诗为乘,以史地民俗的资料为载,则固无不同。鄙人不敢自信懂得诗,虽然如竹垞《棹歌》第十九首云:姑恶飞鸣触晓烟,红蚕四月已三眠,白花满把蒸成露,紫椹盈筐不取钱。这样的诗我也喜欢,但是我所更喜欢的乃是诗中所载的“土风”,这个意见在上文已经说过,现在应用于竹枝词上也还是一样的。
我在《十堂笔谈》中又说:“我的本意实在是想引诱读者,进到民俗研究方面去,使这冷僻的小路上稍为增加几个行人,专门弄史地的人不必说,我们无须去劝驾,假如另外有人对于中国人的过去与将来颇为关心,便想请他们把史学的兴趣放到低的广的方面来,从读杂记的时候起离开了廊庙朝廷,多注意田野坊巷的事,渐与田夫野老相接触,从事于国民生活史之研究,此虽是寂寞的学问,却于中国有重大的意义。”散文的地理杂记太多了,暂且从缓,今先从韵文部分下手,将竹枝词等分类编订成册,所记是风土,而又是诗,或者以此二重原因,可以多得读者,但此亦未可必,姑以是为编者之一向情愿的希望可也。
一九四五年七月二十日,北京。
……
前言/序言
关于《过去的工作》止 庵
《过去的工作》一九五九年十一月由香港新地出版社出版,署名知堂。周氏作《解放后译著书目》,于《过去的工作》和《知堂乙酉文编》之下有云:“以上两种本系一书,为解放前所作杂文,总名‘乙酉文编’,由曹聚仁君携赴香港,为谋出版因析而为二。”《过去的工作》收文十五篇,作于一九四五年四月至十二月(《谈胡俗》篇末未注明写作日期,据周氏手订目录,为一九四五年六月三十日),其中抗战胜利后所写七篇。集中文章当时基本上未曾发表。《关于竹枝词》又见于《知堂乙酉文编》。
《过去的工作》写于《立春以前》之后,也包括“正经”与“闲适”两类文章。闲适之作同样未必闲适,如《谈胡俗》由文化现象入手,却归结到民族整体维系力上去,说来还是正经的。而这问题周氏的确很关注,此前在《汉文学的前途》中说:“反复一想,此是何物在时间空间有如是维系之力,思想文字语言礼俗,如此而已。”他谈及有关事情,更多还是在陈述事实,也就是表现一种信心,即“中国民情之可信托”。这里谈到胡俗,就说:“这些习俗的留遗似乎也很是有限。”或者亦不无现实针对性,仿佛《十堂笔谈》说的:“在今日中国有好些事情,我觉得第一应先应用政治的看法去看”集中文章写法,基本延续此前风格,《饼斋的尺牍》等三篇别具一格,乃是将惯用的“文抄公”写法移植于怀人之作。其中与记述对象的关系略有差异,关于陈独秀限于交待,对待钱玄同、刘半农则是深情怀念矣。怀人之作如此写法,又如此具情感深度,说得上是炉火纯青了。
集中最有分量的,大概还属《凡人的信仰》、《过去的工作》和《两个鬼的文章》这几篇,它们与《药堂杂文》、《苦口甘口》中的“正经文章”一脉相承,而《苦口甘口》以来所做系统总结工作,至此也告完成。所谓系统总结,实际上是一种自我定位。《凡人的信仰》梳理人道主义思想发展脉络,《过去的工作》介绍最关注的几项工作,《两个鬼的文章》比较“闲适”“正经”两种文章,最终都归结到一点上,即苏雪林多年前讲过的:“但我们如其说周作人先生是个文学家,不如说他是个思想家。”(《周作人先生研究》)而这早已是周氏自己的想法,在为集子所作序跋中反复说起,并非一时强调。《两个鬼的文章》说:“我的反礼教思想是集合中外新旧思想而成的东西,是自己诚实的表现,也是对于本国真心的报谢,有如道士或狐所修炼得来的内丹,心想献出来,人家收受与否那是别一问题,总之在我是最贵重的贡献了。”这里有三层含意:一是思想的性质与来源,一是思想家的启蒙主义者色彩,一是思想所具有的终极意义。二三两点不无矛盾,然而一为动机,一为结果,或者说思想家(无论出于主观还是客观的原因)最终超越了启蒙主义者。这乐观地讲,是“思想革命尚未成功”(《过去的工作》);悲观地讲,是“从学理来说人的前途显有光明,而从史事看来中国的前途还是黑暗未了”(《凡人的信仰》)。然而思想的价值并不因此而受到减损。《过去的工作》和《两个鬼的文章》特别像是当作遗嘱写的。以后周氏虽然尚有整整一个写作时期,但是思想不复有太大进境,只是时时仍然体现于作品之中。散文风格此后也有明显变化。自《夜读抄》开始的创作中期,至《过去的工作》(以及《知堂乙酉文编》中写于一九四五年的篇章)完成遂告结束。
此次据新地出版社一九五九年十一月初版本整理出版。原书前有照片八页,分别为“作者摄于北京苦雨斋前”,“作者近年所书墨迹之一”(《苦茶庵打油诗》之十五),“作者题跋墨迹”(题刘半农钱玄同合影),“作者近年所书墨迹之二”(《往昔三十首》之《东郭门》),“作者原稿墨迹之一”(《东昌坊故事》原稿一页),“作者原稿墨迹之二”(《曲庵的尺牍》原稿一页),“作者原稿墨迹之三”(《凡人的信仰》原稿一页)和“作者诗稿墨迹”(《儿童杂事诗》丙编之《鬼物》二首);目次二页,正文七十九页。
用户评价
这套“自编集”最大的价值,或许在于它提供了一个观察“语感”演变的时空隧道。周作人的文字,早期的稚嫩与后期的圆融,其间的过渡是极其微妙的。作为读者,我们得以近距离考察他是如何一步步搭建起自己那套标志性的“周氏语汇”的。那种夹杂着日文的特有语法结构,那种对古籍的信手拈来,以及对白话文潜能的精准拿捏,都不是一朝一夕能练就的。我注意到书中有些篇目,其语言密度极高,每一个词语的选择都像是经过了反复的称量,既要保持典雅,又不能显得晦涩。这种精炼到了极致的文字,读起来需要“慢放”,需要反刍。它不像某些当代散文那样追求一泻千里,而是像精雕细琢的微雕作品,每一个微小的笔触都蕴含着深意。对于文学专业的学习者而言,这套书简直就是一本活生生的、关于“如何写出属于自己的声音”的教科书。它展现了,真正的“文体建立”,是基于深厚的学养和不懈的自我校正。
评分坦率地说,这本书的选篇结构,初看之下似乎有些散漫,缺乏那种传统意义上“连贯的叙事线索”。但正是在这种看似随性的排列中,我看到了周作人先生独特的“时间观”。他似乎并不在意作品之间是否有明确的主题递进,而是将它们视为一个个独立的“瞬间切片”,共同构成了他精神世界的版图。这种编排方式,反而更贴近人真实的记忆模式——记忆本身就是碎片化的,是感官刺激与情感残留的随机组合。我尤其欣赏其中几篇关于“闲适”和“趣味”的论述,它们避开了当时文学界热衷的宏大政治口号,转而深入探究个体精神的自洽与安宁。这是一种极具个人色彩的抵抗方式,以一种近乎“无用之用”的姿态,守护住了知识分子的内心疆域。对于那些习惯了快餐式阅读的读者来说,这本书可能需要耐心去“磨”,去适应那种不紧不慢的节奏,但一旦沉浸进去,就会发现这种慢,恰恰是通往深刻理解的必经之路。它教会我们如何从日常的重复中,提炼出不朽的意义。
评分这套书简直是文人墨客的“考古现场”!我刚翻开目录,就被那种扑面而来的旧时光气息给镇住了。周作人先生的文字,仿佛是陈年的老酒,初尝时或许觉得平淡无奇,细品之下,那股子淡雅、内敛的韵味才缓缓渗出来。他不像鲁迅那样笔锋犀利、直指人心,周作人的笔下更多的是对日常琐碎的细腻捕捉,对市井百态的温和观察。读他的文章,总有一种坐在老式木椅上,透过泛黄的玻璃窗,看外面雨丝纷飞的宁静感。那种对生活细节的敏感度,对于一个生活在信息爆炸时代的读者来说,简直是一种奢侈的享受。他谈论的那些寻常事物——无论是雨声、菜蔬还是孩子的游戏——都被他赋予了一种哲学上的重量,但又处理得轻描淡写,不着痕迹。这本书集合的这些“过去的工作”,无疑是了解他思想脉络和文风形成的关键钥匙。它没有宏大的叙事,只有无数个精巧的侧面,勾勒出一个完整而复杂的文学灵魂。每一次阅读,都像是在跟一位学识渊博的老者促膝长谈,他会不经意间抛出一个你从未想过的角度,让你对生活生出新的敬意。
评分说实话,初读时我带着一种审视的眼光去“挖掘”其中的时代局限性。毕竟,周作人先生的经历和立场在历史的长河中总是伴随着复杂的争议。然而,令人意外的是,当真正沉下心来阅读这些“过去的工作”,那些沉重的历史包袱似乎被神奇地稀释了。剩下的,是纯粹的、文本层面的魅力。他笔下那些关于“苦涩中寻求一丝甜蜜”的描摹,那种对人性复杂面的洞察,超越了具体的政治背景,具有了某种永恒的普适性。这套选集,巧妙地避开了那些最容易引起争论的“时评”,而是侧重于他内心世界的营造。读完后,我得出的结论是:评价一个作家,我们或许永远无法绕开他所处的时代,但通过精选的作品,我们至少可以先抵达他思想的内核,那里是相对纯净、不受外界喧嚣干扰的“象牙塔”。这并非是粉饰太平,而是尊重文本本身的独立价值,允许我们在艺术的层面上,与作者进行一次纯粹的、不带预设的对话。
评分这本书给我的最深感受,是一种“失落的优雅感”。在今天这个充斥着焦虑和效率至上观念的社会,周作人的文字提供了一个完美的避风港。他谈论的“生活美学”,不是那种物质堆砌出来的奢靡,而是一种从精神深处散发出来的从容与雅致。比如他如何对待器物,如何看待一顿简单的餐食,都体现了一种“活在当下”的专注力,一种对“小确幸”的深刻体悟。这种优雅,是建立在强大的学识基础之上的,但表现出来却异常克制。它不是张扬的,而是内化的,像深海的宝藏,需要潜得足够深才能触及。这套自编集,就像是一份精心准备的下午茶,茶具考究,茶水清冽,虽然过程缓慢,但回味悠长。它提醒我们,真正的文化修养,不是学会多少新潮的词汇,而是如何将最朴素的生活过出诗意和格调。对于希望提升自己精神气质的读者来说,这本书是极佳的参照系。
评分慢慢收集周作人的自编集,目前收集了15本,为下一步看鲁迅全集做准备
评分慢慢收集周作人的自编集,目前收集了15本,为下一步看鲁迅全集做准备
评分我把整理出版《周作人自编文集》视为一生主要工作之一;事实上也是如此,整整忙了两年时间。我读苦雨斋的书,始于十五年前,最早接触的是上海书店影印的三种,即《知堂文集》、《知堂乙酉文编》和《过去的工作》,内容不说,单那形式就给我留下很深印象。以后读到周氏著作各种选本,都不能令人满意。作者生前编定一本本集子,无不花费一番心思。而且不像鲁迅惯用编年方法,一本书中文章排列顺序,乃是别有安排,好比营造一种语境,后人打散重编,这语境也就破坏了。岳麓书社曾经大致依照原样出过其中十几种,说来甚合我意,可惜中止了;如果当初此事得以完成,我倒是乐得只当读者。而没来得及出的那些,却是平常不大容易见到的。一度我打算接着做下去,先是编辑出版了《关于鲁迅》,内收《鲁迅的故家》、《鲁迅小说里的人物》和《鲁迅的青年时代》;继而计划把自《秉烛谈》至《过去的工作》各集合刊一部“知堂十种”,却未能如愿。后来再读岳麓版诸书,觉得装帧未免简陋,校改略嫌过头,所以下决心整个儿重做一遍。恰好与出版社方面不谋而合,于是就动手做起来了。
评分《红色骑兵军》是巴别尔毫无争议的代表作,由三十六个短篇组成。每篇小说既独立成章,彼此之间又并非毫无关联。这样的结构类似于福克纳的《去吧,摩西》,你可以把整部小说集当成一部长篇来看。我最喜欢其中的《多尔古绍夫之死》、《政委康金》、《盐》(据称是博尔赫斯最珍爱的作品)、《寡妇》、《拉比之子》、《千里马》、《吻》。尤其是《拉比之子》,对人物刻画之准确、巧妙都很有典型意义。
评分此次据香港三育图书文具公司一九六一年二月初版本整理出版。原书前有作者照片及手迹二页,目次二页,题记一页,正文一百五十四页。目次、正文中“无生老母的消息”均作“无生老母的信息”,兹据手订《乙酉文编》目录改正。
评分非常喜欢周作人的作品,活动时买的。在京东买书很放心。
评分1922年,在“非基督教运动”高潮中,他和钱玄同、沈士远、沈兼士及马裕藻发表《信仰自由宣言》,重申信仰自由的精神。
评分抗日战争爆发
评分我们说周作人的散文是冲淡而不是平淡,还在于周作人的散文是有思想的,它并不让人觉得苍白贫乏。周作人虽然说不上是卓越的思想家,但对于许多事情他都有自己的看法。无论是与非、曲与直、真与假、善与恶、美与丑,他都能判断分明,做到不含糊其辞,模棱两可。对于有些问题的看法,其深刻性往往为一般人所不及。这也正是他的散文不显疲弱,比较耐读的主要原因。当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逝世之后,社会各阶层对他有种种评价。其中不乏恶意的攻讦和指责。周作人即明确指出:孙中山不是“神人”,“也有缺点”,却应“整个地去看出他的伟大来。”如《故乡的野菜》,在艺术手法上可以说完全是采用“白描”的手法。用白描而能写出真挚的感情,只有周作人这样的散文大家才能达到这样的境界。文章开头,周作人便声言他对于故乡没有什么特别的情份,只因为朝夕会面,逐成相识,正如乡村里的老邻居一样,虽然不是亲属,别后有时也要想到他。待我们读完全文,便会发现周作人对野菜的谈论,无一处不掩藏着他眷恋故乡的深情。周作人散文创作表现出的冲淡平易,决不是直露平庸,更不是淡而无味,其中充满了作者的感情。文学创作的生命在于有感情,这对于诗和散文尤其如此。问题是,周作人散文中感情的流露有其特有的方式,那就是抒情的淡化和节制。周作人的散文,总是喜欢把很在意的事说得似乎很不在意,把很有情的事写成似乎颇不经意。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内容均为互联网搜索引擎提供的公开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储任何数据与内容,任何内容与数据均与本站无关,如有需要请联系相关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于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6 book.cndgn.com All Rights Reserved. 新城书站 版权所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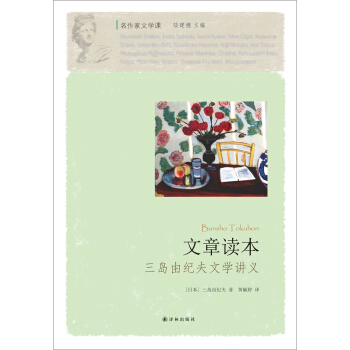
![经典故事轻松读-中国古代寓言故事 [7-10岁]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qciss.net/11643297/54d40c14N97c04ee5.jpg)
![麦克米伦 零时差·YA书系 托德日记 [11-14岁]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qciss.net/11650303/555463bdNf28a058a.jpg)
![汤小团系列·汤小团2:王者之剑(东周列国卷) [7-10岁]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qciss.net/11653199/54e18f5dN07f1aab3.jpg)
![老鼠记者新译本54 狂鼠报业大战 [7-14岁]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qciss.net/11749174/55cd46c9N14e344e4.jpg)



![笨狼的故事:笨狼去旅行(注音版) [3-6岁]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qciss.net/11273483/rBEhU1MvpqsIAAAAAAOxwho8V4sAAKnHgOMs7UAA7Ha666.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