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具体描述
编辑推荐
再访天竺 自明中土
在想像世界版图的“西方”时,尚有一个离感官更远而脚程更近的“西天”。
中国须要深切思考印度、亲近印度是为了自明。
★印裔美籍历史学家、汉学家杜赞奇,自选具代表性的研究文章结集再版。杜赞奇曾为美国历史教科书《东亚史》编写者,因对中国的极大兴趣和研究成果而赢得世界声誉;
★新收录“族群,国家与可持续发展:有关泰戈尔的当代性关联”一文,重新思考泰戈尔近百年的思想、目标和策略,以今人眼光探究泰戈尔关于民族问题、亚洲或所谓“东方”及世界问题的概念化论述;
内容简介
文化、权力、民族国家,是贯穿杜赞奇学术研究的关键词,他始终在探索这样的问题:现代国家如何构造新的文化?如何从历史的极权话语里找回被压抑者的声音,以及民间团体如何“抵抗”来自上面的“攻击”。
《历史意识与国族认同:杜赞奇读本》收录了五篇杜赞奇的代表性文章。其中,“复划符号:关帝的神话”一文,通过研究关帝神话的衰落和破灭过程、由清朝到共产主义革命的中国历史转型,揭示了在帝国政体中,神话与仪式作为一种交流手段的重要性;“中国与印度的现代性批评者”一文,通过将中国与印度的历史作对比,杜赞奇考察了另一种话语,在以现代性为导向的、西方的、启蒙主义的文明史语境之外,“小写”的文化及文明。尤其在“历史意识与国族认同”一文中,杜赞奇重点考察了中国如何从一个儒家、帝制社会转变成为一个现代民族国家,以及与其他非西方社会相对比,中华帝国拥有哪些能促成其转变的特点。
作者简介
杜赞奇,历史学家、汉学家,早年就学于印度,后去美国求学,拜汉学家孔飞力为师,现为新加坡国立大学莱佛士人文教授,并任人文和社会学研究主任,同时也是芝加哥大学历史学荣休教授。
代表作《文化、权利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民族主义话语与中国现代史研究》。前者先后获得1989年度的“美国历史学会费正清奖”以及1990年度的“亚洲研究学会列文森奖”,被奉为社会历史学的必读经典。
目录
复划符号:关帝的神话
中国与印度的现代性批评者
评汪晖的《反思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
历史意识与国族认同
族群,国家与可持续发展:有关泰戈尔的当代性关联
Superscribing Symbols:
The Myth of Guandi, Chinese God of War
Critics of Modernity in India and China
Commentary on Wang Hui's "Rethinking Rise of Modern Chinese Thought"
Historical Consciousness and National Identity
Community, Nation and Sustainability: The Contemporary Relevance of Tagore
精彩书摘
历史意识与国族认同
大多数中国人都为他们悠久而连续的文明深感自豪。有些人还宣称其历史有五千年之久。但事实上,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中国革命者对于这造就了奴隶与封建思想的数千年文明却抱有矛盾甚至否定的态度。现代历史意识在中国的变迁,准确地反映了当权者与知识分子在寻求建立新中国和中华民族身份认同的过程中,为之争论不休的到底是怎样一种国家和社会。换言之,如果我们希望了解中国领袖与中国人民是如何看待他们的社会及其他们在世界上所扮演的角色,那就必须去了解中国人不断变化的历史观。
过去一百年间,那些努力想要理解中国现状的学者和政治家们都专注于一个核心的历史问题,即中国从一个儒家、帝制社会到一个现代民族国家(nation�瞫tate)的转变过程。与其他非西方社会相比,中华帝国拥有一些能促成其转变的特点。当然,也会有一些特点阻碍其转变。促使其转变的特征包括:统一的官僚制国家,拥有社会责任感、政治化的士绅阶层,一个相对开放、较少世袭职位的社会,以及一个高度发展的前工业化经济和大批企业家人才。
另一方面,也存在许多障碍。例如,从19世纪下半叶起,帝国主义列强的入侵和剥削导致政府被大大削弱。此外,官僚及贵族精英代表了位于社会顶层的少数,他们无力——且常常反对——对资源和人力进行有效的调配,而此种调配对一个竞争性的资本主义世界甚为重要。近代中国民族主义之父孙中山时常抱怨,人民就像“一盘散沙”,无法为民族的共同目标而凝聚起来。20世纪初的政治家,例如梁启超,就注意到,如果没有一种积极向上、进步主义的历史观,中国社会无法把它自己当作一个有前途的国家来看待。
事实上,现代意义上的历史书写,于18世纪末的欧洲与民族国家同时诞生,并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非西方世界出现。这种类型的历史书写,常常先播下“民族国家”这个概念的种子,然后逐渐灌输对民族国家之爱和对民族敌人之恨,并创造出在新世界里为国家服务的公民。在这种新的历史观中,民族国家——本国的人民与文化,而非王朝与贵族——才是历史的集体能动力或主体。由于当时大多数历史书写的目的在于重新发掘一个共同的,或有可能被统一起来的、可以实现他们的现代使命的“人民”的概念,因而,国家本身的线性嬗变过程就具有一种推进作用。而当时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世界观无疑又进一步催化了这种作用。根据当时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如果一个国家不能成为一个强大的民族国家(殖民地亦是如此),这个国家就注定将永远被殖民,就注定要灭亡。
不用多说,中华文明拥有复杂而丰富的历史写作传统。例如,由汉代(公元前206年—公元220年)伟大历史学家司马迁所记录下来的历史就拥有一个相当现代的关于时间的概念。他呼吁要为新一代设立新的体制。但毫无疑问,这种线性的时间观在历史写作中并非主流。在帝国晚期(约10001911年)编著的大部分史书都力图回到古代的理想圣贤君主时期,充满着“厚古薄今”的情怀。此外,王朝的编年史家们也趋向于把事件记录成一种循环宇宙论模式的表现,人在其中与超自然力量紧密相连。因此,自然灾害,如水灾,或推翻某个王朝的起义,都被理解为上天对君主与官僚的不满,他们道德败坏,以至于上天收回了其政权的合法性。
因此,进化论或进步主义的时间观认为人总是可以改变未来,而中华帝国的历史学却并不这么认为;换言之,未来的发展是被称为“历史”的实体的一个组成部分。莱茵哈德·科塞勒克(Reinhart Koselleck)把“历史时间”的现代理解总结为“过往经验”和“未来期待”之间的断裂,人们开始期待一个不同的未来,而非期望过上祖先曾经经历过的生活。过去与未来被线性地连接起来,但后者与前者却并不相同。尽管在普通人的历史观中,这不是什么大问题,但对于全球的历史学家和其他思考民族问题的人而言,要与过去保持一致或与过去紧密相连,同时又前行并开创与过去完全不同的未来,乃是一大难题。
在19世纪末的中国,儒士和心忧天下的其他人均认为,日本及西方帝国主义者将瓜分满清帝国(由满洲人于1644年建立),作为一个文化与政治实体的中国将不复存在,这时他们便开始放眼世界,不仅寻求新的军事技术,同时也寻找能够让中国在现代世界生存下来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体制。随着他们为解决方案而争辩,他们也开始吸收时间与历史的新概念,作为对新世界的最基本构想。线性、进步、人类的历史观成为理解他们自己的社会、过去及未来的前提条件。
梁启超与《新史学》
到了20世纪早期,中国历史开始从中世纪的、专制的宰制中解放出来,以启蒙模式来书写。历史学家梁启超——他有可能是第一位以进步的历史观书写中国历史的人——明确指出,一个民族如果没有一部线性发展的历史,它不可能成为一个国家。他于1902年撰写的世界史《新史学》不仅仅是一本描述欧洲征服世界的书,而且是从给世界带来启蒙的欧洲角度进行撰写的。如果说他以前的老师康有为把进步的观念带入了儒家史学中,那么,梁启超的叙述则代表了对中国传统史学的全盘否定,因为传统的历史书写方法无法给中国的民族国家历程赋予意义。
20世纪初,这种欧洲模式经由日本传来中国。当时,明治时期(18691912)的历史学家已在撰写一种将日本民族和文化合为一体的新历史。他们使用如历史分期和考古学等技术来建立日本历史的起源与持续性。为了回应欧洲以“文明教化使命”为理由对各国进行征服的历史叙述,日本历史学家力图在民族历史的基础上发展出一部东亚文明史,这部历史将记下东亚地区时代精神的进步轨迹。在接下来的几十年中,这段东亚文明历史(日本人称之为“东洋史”)被一部分历史学家利用,以此赋予日本作为进步的古代文明领导者占领中国及亚洲其他地区的合法性。
在中国,梁启超的《新史学》想要利用上世、中世和近世的分期方法写一部兼具解放性和连续性的历史。他批评把历史按照朝代划分从而忽略了国民传统的中国史学。在梁启超的分期方法中,中国的上世史“自黄帝以迄秦之一统”(公元前221年),“是为中国之中国,即中国民族自发达、自竞争、自团结之时代也”。中世则自秦统一后至清代乾隆之末年(1796年)。在这段时期里,中国“为亚洲之中国”,即中国的民族与亚洲其他地区的各民族进行交往,并发展出它的一套中央集权。尽管中亚各个种族的势力常常超过汉人,但汉族在精神上掌控着其他民族。到了中世的后期,亚洲民族(我相信他指汉族和中国在中亚的其他邻居)统一起来形成了一个伟大的种族,对抗外族。在近世史中,中国为“世界之中国”。此时,中国民族联合全亚洲民族共同摆脱专制统治,并与其他西方国家竞争。的确,梁启超的历史观与民族国家的关联甚为紧密,为了解释线性历史的分期,他曾把历史分期比喻为民族国家以条约划定各自管辖范围。
在此模型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孕育了真正的中国——一个“是为中国之中国”——的古代时期。上古是一个创造了民族及文化的时期,纯粹且原初。中世则是一个衰落的时期——内部积弊、外来蛮族以及专制制度都在削弱民族的纯洁性。尝试进行精神革新的努力只获得了暂时的成功。近世则是一个革新的时期——且常常是通过斗争取得的。近世还是一个充满着变化的时期,向进步的方向变化。近世可能由复兴揭开序幕,也可以没有复兴而进入近世。当然,民族复兴的理念让近世拯救失落的历史的过程更具戏剧性。在一个现代民族迈向新纪元的进程中,总会遇到重新建构与过去历史的联系的问题,不论这个过去意味着中世纪遗风、儒教、蛮族统治或迷信。因此,整个机制的运作将恢复文化的连续性以及民族的连续性,即使这个机制允许历史学家否定这些可以被用来塑造未来的东西。
从此之后展开的对中国历史进行分期的工作都是基于梁启超提供的基本框架。但这个框架有相当多的争议。争议中的不同立场常常是由参与者不同的政治观点所造成的。其中一个至今仍然持续的争议是关于中华民族的组成结构。汉族是中国的主要民族,占据了人口的90%。中国是汉族的国家吗?中国人是否包括许多我们今天称为“少数民族”的人:例如满族、蒙古族和回族,以及其他在帝国周边地区的更小的族群?尽管这些“少数民族”的数量很少,他们在历史上占据的区域却占了三分之二个满清帝国。他们以及他们所占有的区域是否应被排除在新的中华民国之外?汉人可否被视作是这个由帝国转变成的民族国家中占主导地位的、更优越的族群?换言之,什么人将构成这个民族国家,及其构成人群之间的相互关系——即身份认同——将会是一个大问题。
……
前言/序言
序:
作为方法的印度
或许是因为过去十二年主编《亚际文化研究》(Inter�睞sia Cultural Studies:Movements)国际学刊,与亚洲各地(特别是印度)的批判知识圈产生了工作关系,所以张颂仁与高士明两位先生会找我一起组织在2010年10月至12月于上海举办的“从西天到中土: 印中社会思想对话”的系列活动,由于理念相通,当然就义不容辞地参与了规划工作。他们分派给我的任务之一是替来访的印度学者的读本写序,给了我这个机会说清楚投入这次印中对话的思想背景。
十几年前推动建立《亚际文化研究》学刊的动力,是在有限能力的范围内去改变既有的知识状况,在学术生产的层面上推动亚洲各地的互动与整合。那个时候我们来自亚洲各地十几个地区二十余位的编辑委员,对客观情势进行分析所产生的共识是: 总的来说,在整个20世纪的历史进程中,亚洲各地的知识圈都是把眼睛往欧美看,一个世纪下来,所有事物的基本参照体系都是以欧美经验为主。百年之中,这个逐步建立起来、极其稳固的知识结构,造成了学术思想上巨大的问题,不仅是分析视野的窄化,把欧美之外该参照的多元历史经验割除,更糟糕的是欧美的知识方式几乎变成了惟一的典范。但是,历史已经证明这套知识根本无法有效地理解、把握与解释我们自身的生存环境。如何透过亚洲不同次区域之间知识圈的互动,能够彼此看到,进而能使得各地的历史经验成为彼此的参照点,多元转化既有的参照座标,才有可能创造出新的、更具解释力的知识方式。就是凭借着这个认识论的共识,我们一起走了十二年。
回头来看,这条路没有白走。虽然基本格局没有太大的变化,但是上述的知识结构正处在被快速地松动当中。过去十二年世界情势的变化,正在确立世界是在走向多元并存的时代: 拉美地区政权左转、东盟加三的形成、中国与印度的崛起、非洲经济持续成长、奥巴马取代布什政权、欧盟成员的继续增加,等等。相较于1980年代末期,东欧、苏联社会主义阵营的解体,美国强权一枝独秀主宰世界的“全球化”感觉结构,过去十二年走向多元政治经济区域的变化,仿佛意味着一元世界的结束。在思想上,原来已经确定、凝固的知识体系,及其所深信不移的价值观,正在快速的崩解当中,以欧美历史经验为基地形成信心十足的解释框架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处于变动的时代,放慢脚步、重新找回世界各地根植于现代历史经验的思想资源,于是成为开创新的知识状况难以跳过的路径。十二年很短,《亚际文化研究》还没做出值得彰显的知识方式,但是至少我们已经上路了,尝试着走“亚洲作为方法”的知识路线。
在亚洲,乃至于其他的第三世界地区,既有主流的知识结构之所以会长期以“欧美作为方法”,还是得归咎于世界史的走向,在以欧美为中心向外旋转的力道下,中国也好,印度也罢,都是以“超/赶”(超英赶美)的基本姿势,学习欧美的事物(当然包括了它的价值观),学术思想、知识生产于是被定位成国家民族现代化工程中的主要环节。姑且不要追究“超/赶”的知识方式中暗藏的陷阱,它是否混淆了规范性的目的与客观的历史解释力,至少可以开始问的问题是,一个多世纪下来,现代化的工程到底把原有的这些所谓后发国家变成了什么长相?民主也好,科学也罢,在学习后的搅拌中,实践出了什么新的模样?换句话说,是不是该停下脚步互相交换一些“超/赶”的经验,在欧美之外的地区之间,互相照照镜子,发现自己从过去变到现在的长相的路径?看清楚了,解释到位了,才能继续走下去,甚至进而发现“超/赶”的知识路线已经走到尽头,该是调整方向的时候了。
如果说知识的目的不是挑空了的为了知识而知识(首先预设了大写真理超越于历史的存在,用来笼罩整个世界),而是为了在世界史的范围内,从多元历史经验的视角,解释各地面对的不同的问题与处境,在相互参照、比较之中,慢慢提炼出具有世界史意义的知识命题,那么,可以说当前所有声称具有普遍主义的理论命题,都不成熟,以欧美经验为参照体系的理论,能够充分解释欧美自身历史就不错了,哪里能够解释其他地区的历史状况?反过来说,对于欧美以外地区的解释必须奠基在其自身历史发展的经验、轨迹当中,不能够简化地、错误地以欧美经验来丈量、解释自身。我想这正是应邀来访的著名的庶民研究(Subaltern Studies)历史学家迪佩什·查卡拉巴提(Dipesh Chakrabarty)称之为“将欧洲地方化”(provincializing Europe)的思想方案,或是2010年7月刚刚过世的沟口雄三教授之所以提出“以中国为方法,以世界为目的”的思想精神之所在。
如果说欧美的历史经验只是一种参照的可能性,特别是它的发展经验与后发地区差距更大,那么它在知识转化过程中是需要被重新调整的。来访的印度女性主义理论家特贾斯维莉·尼南贾纳(Tejaswini Niranjana)提出的策略,就是必须在欧美之外的地区开展出“替代性的参照框架”(alternative frame of reference),也就是把原来的以欧美为参照,多元展开,以亚洲内部、第三世界之间的相互参照,经由参照点的移转,从差异中发展出对于自身历史环境更为贴近的解释。这里思想方案的前提是: 关起门来,以本土主义的自闭方式所产生的国粹主义,无法看清楚已经卷入现代的自我,只能沉溺在光辉的过去让自己继续感觉良好而已;打开门来,只以欧美为超赶的参照方式,已然失效,必须在民族国家内部的本土主义(nativism)与欧美中心的世界主义(cosmopolitanism),此两者之外,寻求新的参照体系。
我认为在上述开启新的知识方式的问题意识下,“作为方法的印度”将会对中国学术思想界产生积极的作用,但是中印之间能够产生对话的前提在于抛弃过去“超/赶”的认识论与知识方式,不能再是以落后/进步、现代化与经济发展的速度等,这些表象来进行比较。用我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得先摆脱、搁置规范性的比较,从分析上入手,看清差异,再开始提出内在于历史的解释。
印、中都是世界级的大国,农民占了人口最大的比例,资料显示印度目前是仅次于中国的第二人口大国,将在2026年达到15亿,超过中国的13��5亿成为最大人口国;2015年印度经济的扩展速度将超过中国。换句话说,抛开其他历史、文化的异同,在社会科学的意义上来说,在世界上所有国家中,对中国最具可比性的就是印度,很难找到其他的地方。
但是,这两个国家也有庞大的差异。印度是多语言、多文化的国家,至今没有统一的语言,国会开会是要经过翻译的,所以很多印度的重要知识分子,如来访的阿希斯·南迪(Ashis Nandy),从来就不认为印度是欧洲意义下的民族国家,而是一个文明体。1947年从殖民地的身份独立,在被大英帝国征服以前,印度地区没有统合的政体,所以独立以后也很难编织出数千年统一的民族历史,必须更为多元复杂地理解它的过去。因为多民族的过去,其中在部分的人口中留下了所谓的种姓制度(caste system),到今天这个社会组织的原则还在运作,政治体制必须要去处理,无法简单地消灭,而是创造机制让底层的人口参与在政治过程当中。由于多语言的社会生存,文化差异与政治运作交叉重叠,不仅形成许多所谓区域性政党,连一些地方性政治人物(如省长),都是以特定语言产生的电影工业中制造出来的明星,以区域性的高知名度,经过普选选出。在此意义上,印度是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民主运作根植于地方,全国性的政党都必须想办法跟区域性政治力量结合,才能进行有效的统治。
对我个人而言,过去十几年进出印度,每次交流都有问不完的问题,因为南亚经验与东亚实在不同,摆在一起后者的情况变得相对单纯,各个国家地区语言统一,民族国家面貌表面清晰,又不是多元政党,等等。这些有趣的差异,原来该是可以好好研究的,但是我大部分的中国朋友,大陆、香港、台湾都一样,把这些差异在已经习惯使用的“超/赶”的思路逻辑下,作了球赛式的比较: 印度太长时间是殖民地,所以中国比较好;印度政治制度是殖民体制的遗留,所以中国比较好,是经过孙中山、毛泽东革命建立起来的(反映的是再次贬低殖民地经验,把战后第三世界主义的世界观丢了);印度有种姓制度,所以中国比较好,封建制度已经消除(但是并不去追问印度过去的因子是如何与当代社会接轨,反过头来看看自己的社会中是如何与过去衔接,这个社会真是不再封建了吗?);印度是多党的问题谈的比较少,台湾的人会暂时忘掉欧洲的多党制,把美国两党制搬出来,说只有两党才进步(但是没法儿去问历史问题,印度的多党,乃至于区域政党是为何形成);还有些人说,印度今天牛还在大城市马路上跑来跑去,哪有中国来得进步,不可以以印度为参照的。总之,如果还是要用简单的“超/赶”逻辑,以欧美树立起来的简单的现代化指标来评比,那就只有等到印度经济超过中国,国力强大的时候,才会进入中国人的视野,现在就继续向天上看吧!
其实,交流必然是双向的,其中会有许多难以避免的错位与误解,举例来说,印度的知识界许多朋友对中国感兴趣,并不是由于它的经济崛起,而是: 中国二战后的社会主义阶段与今天经济发展的关系,长远形成的农民文化与政治的关系(这是以帕沙·查特吉[Partha Chatterjee]为代表的庶民研究关切的核心议题),社会主义体制与女性解放的问题至今产生了哪些变化,中国如何看待经济发展与资本主义体系之间的关系,中国广大的知识界对于世界的未来有什么不同于欧美的看法,知识界如何在自身的历史实践中提炼出对世界史的解释,等等。总之,以印度为代表的第三世界知识分子,对于中国有基本的尊重,对中国知识界有一定的期待,都与中国社会主义的政治传统有着密切的关系,而与中国是否现代或是进步没有关联,但是,上述这些问题似乎并不是中国知识界感兴趣,或是准备好可以充分对话的。(更让人难过的是,当第三世界地区期待与中国对话时,常常发现中国许多的知识分子对他/她们根本不感兴趣,眼里只有欧美跟自己,还有人跟你说,别搞政治正确了,亚洲根本不存在,第三世界有什么值得对话的。)
用户评价
这本书的书名本身就勾起了我浓厚的兴趣——“历史意识与国族认同:杜赞奇读本”。“历史意识”这几个字,在我看来,远不止于对过去事件的简单记忆,它更关乎我们如何理解当下,以及如何塑造未来。它是一种审视,一种反思,一种对时间长河中人类选择与命运的哲学拷问。而“国族认同”则是一个在当今世界越发复杂且充满争议的议题。它涉及到我们是谁,我们属于哪里,以及我们在全球化浪潮下如何保持自我。这本书将这两个概念并置,并冠以“杜赞奇读本”之名,预示着它将引领我们进入一个由这位深刻的思想家所构建的理论框架,去探索历史叙事如何被用来构建、维护甚至颠覆国族认同的复杂过程。我期待它能揭示那些隐藏在宏大历史叙事背后的权力运作,以及个体如何在这些叙事中找到自己的位置,或是被这些叙事所塑造。究竟是历史塑造了国族认同,还是国族认同在反过来选择和重塑历史?这是一个我一直在思考的问题,这本书或许能提供给我一些令人耳目一新的解读。我对书中可能出现的案例分析充满了期待,希望能看到具体的历史事件是如何被不同群体以不同方式解读,从而服务于不同的国族认同建构。
评分“历史意识与国族认同:杜赞奇读本”这个标题,一下子就抓住了我对社会建构论的兴趣。“历史意识”听起来不是对过去事实的简单认知,而是一种主体建构的过程,是集体对历史的感知、理解和赋予意义。而“国族认同”,更是社会心理学和政治学中的核心议题,它常常需要一种共享的过去来维系。这本书将两者结合,并以杜赞奇的名字命名,这让我对书中可能蕴含的深刻洞见充满期待。我好奇杜赞奇是否会从符号学、话语分析或者记忆研究的视角切入,来剖析历史如何被“表征”为一种国族叙事。他可能会探讨,在 nation-building 的过程中,哪些历史事件会被选择性地放大,成为国家英雄主义或受难史的标志?哪些历史叙事又是被压制或边缘化的?这本书的“读本”形式,则暗示着它可能是一系列精心挑选的文本集合,能够系统地展现杜赞奇在这一领域的核心思想。我期待它能够提供给我一种新的视角,去审视那些我们习以为常的国家历史叙事,去质疑那些看似天然的国族身份认同。尤其是在全球化和移民涌入的背景下,传统的国族认同面临挑战,这本书或许能为理解这些挑战提供理论上的支持。
评分当我在书店看到《历史意识与国族认同:杜赞奇读本》时,我的思绪立刻被吸引到了历史学的宏大叙事与个体身份构建之间的微妙联系。我一直认为,国族认同并非天生,而是在历史的进程中,通过不断的讲述、记忆和遗忘,逐渐被塑造而成。而“历史意识”这个词,在我看来,正是这种塑造过程的核心要素。它关乎我们如何看待过去,如何从中汲取教训,以及如何将这些理解内化为集体身份的一部分。这本书以杜赞奇的视角呈现,更是让我对其深度和广度充满信心。我猜想,书中不会简单罗列历史事件,而是会深入探讨历史叙事的权力运作,以及它如何服务于特定国族群体的利益。我特别期待书中能有关于“虚构传统”、“国民神话”或“集体记忆操纵”等方面的论述,因为这些都是在构建国族认同过程中常见且重要的手段。这本书的“读本”形式,也让我觉得它是一份极具价值的入门或深化阅读材料,能够系统地呈现杜赞奇关于此主题的精辟观点。我希望能从中学习到如何更批判性地审视那些被奉为圭臬的国家历史,以及理解在多元文化和身份认同日益复杂的今天,国族认同的变迁与挑战。
评分我之所以会对“历史意识与国族认同:杜赞奇读本”产生强烈的购买冲动,很大程度上源于我对现代社会中个体与集体身份之间复杂互动的迷恋。在信息爆炸的时代,各种声音和叙事争奇斗艳,我们似乎每天都在被不同的历史版本所包围。这本书的书名直接点出了这种张力:历史并非静止不变的客观事实,而是在不断被“意识”和“解读”,而这种解读往往与我们所属的“国族”紧密相连。我好奇杜赞奇这位学者,在“读本”的形式下,将如何梳理他对于这一议题的核心观点。他是否会侧重于理论构建,还是会辅以大量的历史实例?我更倾向于后者,因为脱离了具体历史语境的理论,往往显得空泛。我希望看到他如何分析某些特定的历史事件,例如战争、革命、殖民经历,是如何在不同的国家内部被建构成不同的“国民记忆”,并进而塑造出具有排他性或包容性的国族认同。同时,“读本”这个词也暗示着这可能是一本精选集,汇集了他关于此主题的最重要、最具有代表性的论述。这意味着我可以快速而系统地接触到他的核心思想,而不必在一堆繁杂的著作中迷失方向。我期望它能提供给我一个批判性思考国族认同的工具,让我不再轻易被那些简化、煽动性的民族主义言论所裹挟。
评分这本书的书名——“历史意识与国族认同:杜赞奇读本”——让我感觉非常契合当前全球社会正经历的深刻变革。国族认同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似乎经历了某种复兴,或者说,在挑战全球化趋势的背景下,它被重新强调和定义。而历史,作为支撑国族认同的基石,自然也成为了被审视和争夺的焦点。我迫切想知道,杜赞奇是如何将“历史意识”这个概念与“国族认同”这个更为宏大的社会政治现象联系起来的。他的理论框架会如何解释,为什么在某些时期,历史的某些方面会被人们格外关注,而另一些方面却被淡忘?我猜测,这背后一定与权力、利益和身份焦虑息息相关。书中是否会探讨,当现代国家试图塑造统一的国族认同之时,历史的多元性、复杂性以及可能存在的矛盾,是如何被处理的?是否存在一种“标准”的历史叙事,以及这种叙事是如何被确立并传播的?我期待能看到一些关于历史教科书、国家纪念日、公共历史项目等具体案例的分析,因为这些都是塑造历史意识和国族认同的直接载体。这本书的“读本”形式,也让我期待能看到一些跨越不同时期、不同主题的杜赞奇的精彩论述,能够构建出一个相对完整的思想图谱。
评分读到“历史意识与国族认同:杜赞奇读本”这个书名,我脑海中立刻浮现出许多关于民族国家形成、历史书写与政治宣传之间关系的画面。我们常常被告知要“铭记历史”,但“谁”来铭记,以及“如何”铭记,往往决定了我们对“我们是谁”的认知。我猜测这本书会深入探讨历史记忆的建构过程,特别是那些被官方或强势群体所选择、强调、甚至是故意忽略的历史片段。杜赞奇的理论,在我有限的了解中,似乎总是带着一种对权力运作的深刻洞察。因此,我非常期待这本书能揭示,在构建国族认同的过程中,历史是如何成为一种工具,服务于特定的政治议程。比如,某些国家可能会刻意突出其辉煌的过去,以激发民族自豪感和凝聚力;而另一些国家,则可能专注于强调其受压迫的历史,以唤起共同的愤怒和反抗精神。这两种策略,殊途同归,都是为了塑造一种“我们”与“他们”的界限,强化集体身份。我希望书中能有对不同国家或民族历史叙事进行对比分析的章节,让我能够更直观地理解这种差异。同时,“读本”的形式也意味着,我可能会遇到一些经过精心挑选的文章,它们能直接展现杜赞奇论证的力度和深度,而不是碎片化的零散观点。
评分“历史意识与国族认同:杜赞奇读本”这个书名,在我的眼中,仿佛是一把钥匙,能够开启对现代社会最深层的身份谜题的探索。我常常思考,为什么在不同时期,人们对于“我们”这个概念的认知会有如此大的差异?为什么某些历史事件会被反复提及,而另一些则被遗忘?这背后,无疑是“历史意识”在起着关键作用。而“国族认同”,更是这种历史意识的集中体现。这本书以杜赞奇的名字冠名,让我对其理论的深刻性和批判性充满了信心。我期待书中能够呈现出,历史是如何被编织成一个关于“我们”的宏大叙事,而这个叙事,又如何反过来塑造了个体和集体的身份认同。我尤其好奇,在多元文化日益交融的今天,传统的国族认同是否还能保持其原有的形态?这本书是否会探讨,当历史叙事出现断裂或冲突时,国族认同又会面临怎样的挑战?“读本”的形式,也意味着我能够系统地梳理杜赞奇关于此议题的思想脉络,从不同侧面去理解他如何分析历史记忆的形成、历史叙事的建构以及这些如何最终汇聚成强大的国族认同力量。
评分看到《历史意识与国族认同:杜赞奇读本》这个书名,我便联想到许多关于国家如何通过塑造共同的历史记忆来凝聚国民的论述。在我看来,“历史意识”不仅仅是对过去的了解,更是一种对历史的解读、反思和情感投射,而这种意识,恰恰是构建“国族认同”的基石。我十分期待这本书能够揭示,在民族国家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历史是如何被用来建构一种普遍的、共享的身份认同的。杜赞奇的“读本”形式,让我认为这将是一本精选集,汇集了他关于此主题最深刻、最有代表性的论述。我希望能从中看到,历史叙事是如何被精心构建,以强调共同的起源、共同的价值观、甚至是共同的敌人,从而强化“我们”的概念。这本书是否会探讨,那些被选择性遗忘或轻描淡写的历史,对于国族认同的形成又有何影响?我更希望能从中学习到,如何以一种更加批判性的眼光去审视那些被奉为圭臬的国家历史,理解历史意识在塑造国族认同过程中的复杂性和权力动态。
评分这本书的书名《历史意识与国族认同:杜赞奇读本》听起来就蕴含着巨大的思想能量,特别是“杜赞奇”这个名字,更是让我对书中可能出现的理论深度充满期待。我一直认为,历史不仅仅是过去事件的记录,更是一种意识形态的体现,一种塑造我们如何看待现在和未来的关键力量。而“国族认同”,则是在这种历史意识的建构下,逐步形成的集体身份。我好奇杜赞奇是如何解析这两者之间相互作用的。他是否会分析,在民族国家构建的过程中,历史是如何被选择性地叙述、强调,甚至发明出来的,以服务于形成一种统一的、排他的国族身份?我特别关注书中可能涉及的关于“他者”的建构,因为国族认同往往是通过与“非我族类”的对比来强化的。这本书的“读本”形式,让我认为它可能是一系列精选的、具有代表性的杜赞奇论述,能够帮助读者快速把握其核心思想。我期待它能够提供给我一种审视历史的全新视角,让我能够更深刻地理解,我们所处的国族身份,是如何被历史的“意识”所塑造的,以及这种塑造过程中的权力与隐喻。
评分当我看到“历史意识与国族认同:杜赞奇读本”这个书名时,脑海中立刻涌现出对现代民族国家如何建立和维系其合法性的思考。我深信,一个国家的凝聚力,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其公民共享的“历史意识”,而这种意识,又直接导向了“国族认同”的形成。我期待这本书能深入剖析,这种“历史意识”是如何被有意或无意地建构起来的。是教科书的编写?是官方的宣传?是文学艺术的创作?还是民间口耳相传的故事?杜赞奇的“读本”形式,则预示着我将能接触到他关于这一主题最核心、最具有影响力的观点。我希望书中能有对具体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的解读,揭示它们是如何被赋予特定意义,并成为国族认同的基石的。例如,一场战争的胜利可能被渲染成民族辉煌的开端,而一次失败的革命则可能被塑造成民族复兴的契机。这本书能帮助我理解,历史并非总是客观公正,它往往是权力博弈和身份构建的战场。我对它能够揭示历史叙事背后隐藏的意识形态,以及这种意识形态如何影响着我们对“我们是谁”的认知,抱有极大的兴趣。
评分历史意识与国族认同:杜赞奇读本
评分帮导师买的,不错
评分书的内容很好,收录的几篇文章都不错。我是冲着杜赞奇的那篇买的,没想到其他几篇也很赞。而且书还收录了这些文章的原文,翻译版和原版可以对照来看,如果出现翻译问题还可以回溯去查,这种安排满好的。总体来说,内容不错,值了。
评分杜赞奇他本来是印度人,后来长期求学、工作和生活在美国,成为一位美籍印裔学者。他又是一位汉学家,浸淫中国历史将近四十年。这样一种特殊的履历,使杜赞奇成为中国人眼中一位特别的海外汉学家。为什么特别?因为他的印、美、中三重背景。这种背景直接影响了杜赞奇的学术研究和各种思想关怀,下面就从他的求学经历以及相关学术研究来简要介绍一下杜赞奇其人其事。
评分准确来说,这本书尚未读过,但这个议题很有吸引力,给个赞先。
评分帮导师买的,不错
评分很好
评分不过,书的字号有点小,看起来有点小费眼。
评分历史意识与国族认同:杜赞奇读本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内容均为互联网搜索引擎提供的公开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储任何数据与内容,任何内容与数据均与本站无关,如有需要请联系相关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于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6 book.cndgn.com All Rights Reserved. 新城书站 版权所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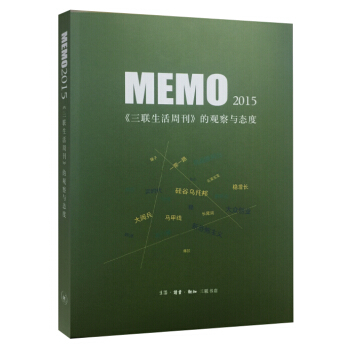
![莎士比亚的动荡世界 [Shakespeare’s Restless World]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qciss.net/11913694/573bec63N511cc12e.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