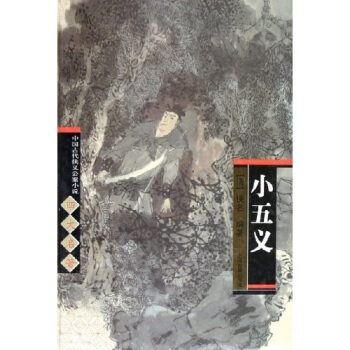具体描述
编辑推荐
《池塘》是哈金一部在英语世界引发关注的长篇小说,是其黑色幽默代表作之一,中国大陆首次出版。这是一本充满深厚幽默感的书,让你笑的同时,心中隐隐作痛。
内容简介
《池塘》为哈金在美国出版的第1部长篇小说,也是哈金的长篇代表作之一。书中的故事发生在一个虚构的地方,主人公是一个在化肥厂里工作,自学成才的知识分子,他因为不满于分房的不公平,用自己的书画才能讽刺有关领导。虽然如愿以偿,但自己也碰得头破血流。这部小说虽然写的是抗争,但书里不但没有伸冤抱怨的戾气,反而有一种喜剧效果。
作者简介
哈金,本名金雪飞,1956年生于辽宁省,曾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中服役五年。1982年毕业于黑龙江大学英语系,在校主攻英美文学,1984年获山东大学英美文学硕士学位。1985年赴美留学,并于1992年获布兰迪大学(Brandeis University)博士学位。现任教于美国波士顿大学(Boston University)。
精彩书评
这是一出彻底的喜剧,戏谑、喧闹、娱乐性十足。哈金以精炼的素朴文字,俚俗的语言,生动呈现中国的面目。
——《纽约时报》
虽然异国情调的主题很吸引人,但是作者讲故事的才能更是这本书成功的因素。
——《时代》
哈金在享誉国际文坛之后,以这样的方式回来,令人欣喜。在我眼里,哈金永远是一位中国作家,因为他写下了地道的和有力的中国故事,虽然他使用了我所不懂的语言。——余华
精彩书摘
一
邵彬在歇马亭已经住了六年多,从心里厌恶这个乡下小镇。他的妻子梅兰整日唠叨,礼拜天洗衣裳也得走上七八里路。梅兰不会骑车,用自行车驮她到蓝溪河去洗衣裳当然是邵彬的事情。邵彬在丰收化肥厂工作,这个月厂子里太忙,星期天也得加班,梅兰只得自己走着去那里。要是他们住在工厂的宿舍区里,走几步就能到河边。这些日子梅兰整日整夜嘴里念佛,求菩萨保佑她家很快能在“工人之村”分到一套房子。
“瞎吵吵啥,这次咱们铁定有份。”星期三下午,邵彬对紧张兮兮的妻子不耐烦了。
“你咋这么肯定?”
“他们应该分给咱一套。我的工龄比别人长嘛。”
“工龄顶啥用?”
邵彬确实在化肥厂干了六年了。厂里分房向来都是依据实际需要和工龄长短,看起来邵彬这次能分到一套新房子。可是梅兰却不那么乐观。“我说,”梅兰对丈夫说,“你就不会给刘书记和马厂长送两瓶‘二锅头’?我可听说每天晚上都有人往这两家跑。你光坐在家里就能把房子等来?”
“你少提这事。我才不为他们花一分钱呢!”
“倔驴。”她叹了口气。
邵彬个子不高,从前也是个健壮结实的汉子。最近几年,他的体重掉得厉害,背地里得了个“瘦鬼”的外号。他长得五短身材,但因为自负有才,骄傲得很。在丰收化肥厂,邵彬看的书比谁都多,可以说是博古通今,甚至还知道福尔摩斯探案的故事。他那两笔字写得更是漂亮。厂里有些女工过去常说他“可惜模样没有字俊”。五年前他和梅兰订婚的时候,大家伙儿都吃惊不小,说他们真是“佳人爱才子”。虽说梅兰不是什么佳人,邵彬也算不上才子,但两人比较起来,她长得就出色多了,有几个小伙子还追她呢!
结婚后,他俩就住在夕阳街上的一间宿舍房里,那是梅兰的工作单位—人民百货商场的房子。现在他们有了一个活泼的两岁女儿,这间二十多平方米的屋子就转不开身了。另外,虽说邵彬在班上是个钳工,下了班可是位业余画家和书法家。艺术家是需要空间的,最理想的是有一个只属于自己的房间,他可以在里面精心构思创作。可这根本是不可能的事情。邵彬只好每天晚上等妻子女儿睡下了才开始拿起毛笔练习书画,桌子上亮着的台灯经常刺得梅兰娘俩睡不着觉。房间里总是充满着浓浓的墨汁味,梅兰不得不在冬天里也开着小气窗。邵彬对此也没有办法,他们多想有一套像样的房子啊!
这些日子,邵彬一直想打听自己的名字是否在分房委员会考虑的名单上,但探不出个究竟。他发现周围的同事们突然变得不声不响、神秘莫测,仿佛一夜之间每人都发了财,对别人起了戒心。
星期四早上,邵彬在给车队修理液压千斤顶的时候,在心里一遍一遍地给自己打气:现在该轮到我分到房子了。昨天晚上,梅兰讲的其他工人给领导送礼的话让他有点心慌。他还是不住地安慰自己不要失去信心。
他没想到当天下午最后的分房方案就贴在厂门口的告示栏上了。邵彬在榜上找了几遍也没有找到自己的名字,顿时火冒三丈,周围那些没有找到自己名字的工人们也都炸了窝。所有的车间里都能听到怨恨的叫声,而那些分到房子的人却一声不吭。有些工人说要立刻写大字报揭发厂领导的腐败行为。也有几个人说,他们要在今天晚上把给厂领导建造的四幢宽敞的宿舍楼里安上炸药,炸个粉碎。但这些不过是图个嘴上痛快,这样的气话以前不知道说过多少遍了,啥事也没有发生过。
下班铃声一响,邵彬就离开了工厂。他心不在焉地骑车回家,一顶军帽斜扣在头上,白汗衫敞着怀,衣服下摆在身后舞动。他满腹心事,脑袋沉甸甸的。回去该咋向梅兰说呢?她一定伤心死了,怎么才能安慰她呢?
化肥厂北面是一个铁路交叉道口。邵彬刚穿过铁轨,就看见厂党委书记刘恕背着手在前面走。邵彬追上去,下了自行车。“刘书记,能跟您说句话吗?”他说。
“行啊。”刘书记停住脚,直了直身子。他那双肿眼泡半闭着。
“我为啥这次分不到房子?”邵彬问。
“你寻思就你一个人分不到啊?还有一百多号住房困难的同志排队等着呢,这情况你知道吗?”
“我在咱厂干了六年了。侯尼娜才来厂三年,凭啥她这次就能分到房子?我不明白。”
刘书记也没拐弯抹角:“这是分房委员会的决定。他们认为她比你更需要房子住。新社会男女平等。你现在还有地方住,可是这些年她一直和家里人挤在乡下。人家一个姑娘不需要个地方结婚吗?因为没有房子,她推迟了两次婚期。你也不能让人家女同志单身一辈子啊?”
邵彬差点叫起来:她能和你一起住啊,不行吗?但是他一个字也没说出来,转身又骑上了那辆“国防”牌自行车,连声“再见”也没说就走了。他一边狠命踩着脚踏板,一边在心里骂着:“王八蛋,你已经有一套大房子了,这次又捞了套更大的。你他妈的是在滥用职权。这不公平,太不公平!”
矮胖的刘书记摇了摇头,冲着邵彬的背影说了句:“傻蛋!”
前言/序言
一个作家的力量
余华
我很欣赏美国笔会在授予《等待》2000年福克纳小说奖时,对哈金的赞誉:“在疏离的后现代时期,仍然坚持写实派路线的伟大作家之一。”
2003年初春的时候,我在北京国林风书店买到了《等待》,然后又见了几个朋友,回家时已是凌晨,我翻开了这部著名的小说,打算读上一两页,了解一下哈金的叙述风格就睡觉。没想到我一口气读完了这部书,当我翻过最后一页时已经是晨光初现,然后我陷入冥思苦想之中。我惊讶哈金推土机似的叙述方式,笨拙并且轰然作响。哈金的写作是一步一个脚印,每一段叙述都是扎扎实实。在他的小说里,我们读不到那些聪明作家惯用的回避和跳跃,这种无力的写作至今风行,被推崇为写作的灵气。作为同行,我知道迎面而上的写作是最困难的,也是最需要力量的。
这个1956年出生的中国人,当过兵,念过大学,29岁时漂洋过海去了美国,获得博士学位,任教于美国的大学,这是那个时代很多年轻中国人选择的康庄大道。可是用英语写作,哈金奇特的人生之路开始了。毕竟哈金去美国时不是一个孩子,已经是一个成年人了,一个带着深深的中国现实和中国历史烙印的成年人,用异国他乡的语言来表达自己故乡的悲喜交集,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可是哈金做到了,他每一部英语小说都要修改二十多遍,并不是为了对人物和故事细节上的把握,而是对英语用词的分寸把握。美国是一个很多方面十分规矩的国家,作为著名的波士顿大学英语文学写作的教授,哈金不能向他的同事请教,更不能向他的学生请教,哈金的太太是一位地道的中国人,她的英语表达能力远远不如哈金,哈金在用英语写作时可以说是举目无亲,只能自己苦苦摸索。
就是这样一位作家,写出来的英语让一些纯种美国人都赞叹不已。而我,一个中国人,读到自己同胞的小说时,却是一部翻译小说。可是这部名叫《等待》的翻译小说,让我如此接近中国的历史和现实,近到几乎贴在一起了。很多生于中国,长于中国,甚至从未离开过中国的作家写出来的小说,为什么总让我觉得远离中国的历史和中国的现实?我读到了太多隔靴搔痒的中国故事了,可是远离中国的哈金让我读到了切肤之痛的中国故事。
我想这就是一个作家的力量,无论他身在何处,他的写作永远从根部开始。哈金小说所叙述的就是中国历史和现实的根部,那些紧紧抓住泥土的有力的根,当它们隆出地面时让我们看到了密集的关节,这些老骥伏枥的关节讲述的就是生存的力量。
《等待》之后,我又读了哈金的《疯狂》,以及零星发表在中国杂志上的一些短篇小说。现在铁葫芦图书即将推出哈金的三部作品,这对于国内的读者认识哈金作品的全貌是件好事。这位美国的少数民族作家,在享誉国际文坛之后,以这样的方式回来,令人欣喜。在我眼中,哈金永远是一位中国作家,因为他写下了地道的和有力的中国故事,虽然他使用了我所不懂的语言。
我难忘第一次在波士顿见到哈金的情景,那天晚上大雨滂沱,哈金带着我们一家三口在哈佛广场寻找酒吧,所有的酒吧都拒绝我十岁的儿子进入,最后四个人在大雨中灰溜溜地来到了旅馆,在房间里开始了我们的长谈。那是2003年11月的某一天。
用户评价
很少有书能让我产生如此强烈的“空间感”。阅读《池塘》的过程,就像是戴上了一副特殊的透视眼镜,我感觉自己能够看到水体深处的构造,闻到不同层次的水草腐烂后的气味,甚至能感受到水温从表层到深处的梯度变化。这完全归功于作者对细节的病态般的专注。他似乎不放过任何一个细微的现象:水黾脚上形成的微小涟漪如何散射光线、某种蜉蝣的蜕变过程需要多少个精确的小时、水面油膜反射出的世界与水下世界的景象是如何叠加的。这种对微小事物的尊重,使得整个叙事拥有了一种近乎神圣的庄严感。它让我明白,一个“小”的世界,只要被足够深入地探索,其复杂性和深度可以轻易超越人类用语言构建的任何宏大史诗。这本书是对“平凡”的一次史诗般的颂歌,它教导我们,真正的奇迹并不在于遥远的星系,而在于我们脚下那片看似不起眼的泥水之中。读完后,我走路时都会不自觉地寻找路边被忽略的水洼,带着一种全新的敬畏之心。
评分读完这本《池塘》,我简直要怀疑自己过去对“环境文学”的理解了。它完全避开了那种惯常的、带着说教意味的环保口号,转而采取了一种近乎考古学家的严谨态度,去“挖掘”这个看似平凡的水域所承载的历史和记忆。我特别欣赏作者在叙事结构上的大胆尝试。它不是线性的,更像是一张错综复杂的生态网络图谱。一会儿聚焦于水面上的浮萍如何通过光合作用悄无声息地改变水体的化学成分,一会儿又跳跃到百年前此地曾经是某个家族的休憩之所,甚至暗藏了某个被遗忘的秘密。这种跨越生物学、社会学和地方历史的编织手法,让“池塘”这个意象获得了惊人的厚度。它不再是一个静态的背景,而是一个动态的、不断自我修正和记录的活档案。尤其赞赏的是,作者在处理人与非人(non-human)要素的互动时,保持了一种近乎冷峻的客观性,既没有过度浪漫化自然,也没有陷入极端的悲观主义,而是在两者之间找到了一个既真实又充满张力的平衡点。这本书要求读者跳出传统的以人为中心的叙事框架,去学习另一种“观看”世界的方式。
评分说实话,我原本以为这会是一本挺“慢”的书,适合在周末的午后慢慢品味,但它的内在驱动力比我想象的要强劲得多。《池塘》的文字有一种非常独特的“粘性”。它用词考究,句式多变,时而如涓涓细流,细密而连绵不绝;时而又像突然爆发的雷阵雨,用一连串短促有力的句子砸下来,让人喘不过气。这种语言上的节奏感,完美地模仿了自然界中那种不稳定的平衡状态。比如,书中描写暴雨将至时,空气中那种静电的紧张感,那种色彩饱和度的骤然提升,通过文字的转化,我几乎能真切地感受到皮肤上泛起的鸡皮疙瘩。此外,作者似乎对“界限”这个概念有着近乎偏执的探索欲。池塘的边界在哪里?是水线,还是水线与岸边植被交界的那一小块泥泞地?从水下到水面,从有光到无光,这些看似模糊的地带,恰恰是全书最引人入胜的地方。它引导我们去思考,我们日常生活中所设定的那些清晰的分类——干净与污秽、生命与非生命、清晰与混沌——其实是多么的武断和脆弱。
评分如果要用一个词来形容阅读《池塘》的整体感受,我会选择“回响”。这本书不仅仅是记录了池塘生态,它更像是一面镜子,反射出了我们现代人精神世界的某种匮乏。作者的叙事语调是疏离的,冷静的,但正是这种冷静,使得其中偶尔流露出的对生命脆弱性的关怀显得格外有力。他没有直接控诉,而是通过描绘那些在自然规律下无力挣扎的生命——比如被突如其来的干旱困住的小鱼,或者被入侵物种挤占生存空间的本土生物——让我们自己去体会那种无声的悲剧。这种叙事的高明之处在于,它将读者置于一个道德审判者的位置上,但又巧妙地让我们意识到,我们自己也同样是这个庞大而冷漠的生态系统中的一个“变量”。全书的收尾处理得非常高明,没有给出任何明确的答案或希望,只是回到了一个永恒的循环:水蒸发、降落、汇聚,生命与死亡持续进行。这使得全书的阅读体验超越了文学范畴,更像是一次对存在本质的冥想。
评分这本《池塘》的书名乍听之下,颇有些宁静致远的禅意,但翻开书页,我才发现它远比我想象的要波澜壮阔,或者说,它将宏大的主题包裹在极其细腻的日常观察之中,让人在不经意间被那种深沉的哲学思考所触动。作者的笔触犹如高倍显微镜下的生物切片,精准地捕捉到了人与自然界之间那种微妙的、常常被我们忽视的权力博弈和共生关系。比如,书中有一段关于水虿捕食的描写,简直是微观世界的史诗,那份冷酷的生存本能被描绘得既残忍又壮美,让人不禁反思,所谓的“文明”在自然法则面前,究竟占据了多大的分量。而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作者对“时间”的感知。在池塘这个相对封闭的空间里,时间似乎被拉伸和压缩了,岸边那棵老柳树的年轮和水底淤泥的沉积,构成了与人类短暂生命截然不同的参照系。阅读过程中,我常常会停下来,闭上眼睛,试图在脑海中重构出那种没有人类噪音的、仅由水声、风声和生物活动构成的世界。这本书不只是在描述一个景观,它在重建一种感知体系,一种更接近大地脉搏的生命节奏感。阅读体验是沉浸式的,需要极大的耐心和专注,但回报是丰厚的——它让你重新审视自己存在的尺度。
评分包装完美,马上开始阅读!实物书特有的质感很好!
评分书本身内容不错,可是印刷质量太差了。好几次都以为是买到了盗版
评分包装完美,马上开始阅读!实物书特有的质感很好!
评分哈金的书,买过好几本了,差这本,补上,待读。从《等待》《南京安魂曲》《小镇奇人异事》《落地》到《新郎》和这本,共六种。其它的不知还会不会出,等待。
评分铁葫芦这回看来是要把哈金出齐了吧。连收三本:《等待》《新娘》《池塘》。
评分很喜欢哈金的作品!
评分喜欢哈金的不能错过
评分挺不错的商品,非常好,而且自营快递很快,客服也很耐心解答我的问题,这次购物非常好
评分好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内容均为互联网搜索引擎提供的公开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储任何数据与内容,任何内容与数据均与本站无关,如有需要请联系相关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于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6 book.cndgn.com All Rights Reserved. 新城书站 版权所有






![异形:走出阴影 [Alien: Out of the Shadows]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qciss.net/12157020/58d2278eN18c7e5ea.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