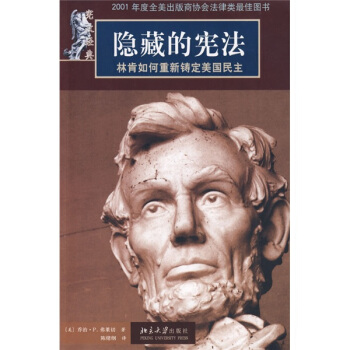具体描述
编辑推荐
《刑法哲学》是一部以犯罪与刑罚及罪刑关系为研究内容的学术专著,是道格拉斯·胡萨克教授的扛鼎之作;是由作者以前发表在诸多哲学期刊、法律评论和书籍中文章的章节组成。其中,很多文章已引起法学教授们的注意,还有很大部分的文章则已为哲学家所熟知。本书内容主要分为四篇,一是刑事责任论,二是罪过程度论,三是辩护事由,四是刑罚及其正当性。内容简介
《刑法哲学》是一部以犯罪与刑罚及罪刑关系为研究内容的学术专著,是道格拉斯·胡萨克教授的扛鼎之作;是由作者以前发表在诸多哲学期刊、法律评论和书籍中文章的章节组成。其中,很多文章已引起法学教授们的注意,还有很大部分的文章则已为哲学家所熟知。本书内容主要分为四篇,一是刑事责任论,二是罪过程度论,三是辩护事由,四是刑罚及其正当性。作者简介
道格拉斯·胡萨克,是世界著名刑法学家,美国著名学府罗格斯大学法学院教授。在刑法学上有着突出的学术成就,他的很多作品曾发表在各大顶尖的法学评论上,且他的作品被翻译成10多种语言广泛传播,享有崇高的世界声誉。其专著《刑法哲学》由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谢望原教授译成中文,在中国具有很大影响,也使胡萨克教授在中国一举成名。目录
导论第一章刑事责任是否需要客观行为?
引言
一、行为要件及道德责任和刑事责任之间所谓的区别
二、行为要件
(一)行为要件的地位
(二)满足行为要件的行为之本质
三、行为要件的评价性要素
四、控制要件
五、基于状态的刑事责任
六、基于思想的刑事责任
结语
第二章犯罪动机和刑事责任
引言
一、犯罪动机的概念
一、动机的重要性
(一)作为与不作为
(二)正当化事由和合理动机
(三)宽恕事由的适用条件
结语
第三章刑法语境下“目的不影响允许性”论的代价
引言
一、目的论
二、目的是如何发挥作用的?
三、目的和犯罪未遂
四、刑法理论的成本
结语
第四章论故意转移
一、故意转移之条件
二、对纯粹主义论的批评
三、故意转移废止主义解决路径
四、故意转移范例引申的十二个非标准性案例
五、法律拟制原理分析
六、运气补偿论分析
七、量刑均衡原则分析
结语
......
精彩书摘
第一章刑事责任是否需要行为要件?引言
刑事责任是否需要行为要件?大多数的法律哲学家都认为应该如此,但笔者并不这么认为。笔者从对该问题本身进行澄清开始,以论证自己的否定回答。如果笔者解释该问题的努力是富有成效的,那么笔者希望刑事责任并不需要行为要件的观点会变得更为清楚。然而,笔者的结论并不是要支持那些认为刑法不具有原则性的批评理论家的观点。参见Alan Norrie,Crime,Reason and History(London:Weidenfeld and Nicolson,1993).笔者也将论述那些支持行为要件的考量因素的观点所提出的另一种不同原则——笔者将这种原则称为控制要件。
笔者希望能够证明控制要件优于行为要件,从而有助于重构和理解实体刑法。批评理论家有可能并不同意此观点,他们会质疑笔者所主张的原则的合理性和一致性。究竟控制要件是否会被认为是合理的或者是否会被认为是一致的,主要取决于两种因素。第一,控制要件的含义必然被证明与刑法的一般性原理和法律原理相冲突。笔者从此点开始对控制要件进行评估,尽管还有其他大量的工作有待完成。第二,批判理论家必须解释通过一致性和合理性他们究竟想要说明什么——据说刑法欠缺这两个特征。而笔者并不想探求后面这个问题。相关的讨论参见R A Duff,Principle and Contradiction in the Criminal Law;John Gardner,On the General Part of the Criminal Law in Duff (ed),Philosophy and Criminal Law(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8).
在该部分内容的第一部分,笔者将分析在评估刑事责任必须具有行为要件方面遇到的困难,同时讨论刑事责任需要行为要件在区分道德责任和刑事责任的条件中所扮演的角色。笔者并没有对刑事责任能力和刑事责任之间的联系进行一般性的分析,而只是认为前者是后者的必要条件。在第二部分中,笔者会澄清刑事责任需要行为要件的论点。第三部分中,笔者会检视认为刑事责任需要行为要件的原因,同时会主张这些论点实际上都是支持另一个不同的结论:刑事责任需要控制要件。在第四部分中,笔者会对控制要件进行阐述。在第五部分中,笔者会将行为要件和控制要件对状态犯罪正当性的影响进行对比:状态犯罪主要是禁止某人是什么而不是禁止他或她做什么。在第六部分中,笔者将把行为要件的含义和针对思想犯罪正当性的控制要件的含义进行对比:思想犯罪是禁止人们企图想做什么。在这两种语境中,控制要件至少看起来更优于行为要件。在证成笔者的观点的过程中,笔者经常会参考米歇尔·摩尔(Michael Moore)的著述,米歇尔·摩尔对行为要件的研究是目前为止最具有思想性和最精细的研究。Michael Moore,Act and Crime(Oxford:Clarendon Press,1993).
一、行为要件及道德责任和刑事责任之间所谓的区别
当代刑法典似乎清楚地规定,刑事责任必须具备行为要件。或者是本应实施某种行为的不作为。《模范刑法典》的Sec201(1)就是这种代表。该条规定:“行为人的责任取决于实施了某个行为,且该行为包括自愿的作为和本应履行某种作为而没有履行的不作为,否则行为人就是无罪的。”因此,如果有一些刑罚理论家不同意这个问题,大家当然会感到吃惊。究竟应该如何解释这种长期存在的异议?解释可能会有很多,但笔者仅仅讨论其中的两种。对此,还可以进行另外的解释。例如,学者之所以对施加刑事责任是否必须具备行为要件存在很大分歧,是因为他们并不确定由法律施加的非难是否属于刑事责任。如果由法律施加的责难并不需要行为要件,那么对于这些非难是否属于刑罚也存在争议。因此,学者在刑事责任是否具备行为要件的问题,会有分歧。实际上,判断某种法律非难是不是施加刑事责任是非常困难的。例如,参见FlemingvNestor,80 SCt 1367(1960).在该案件中,法院在终止了先前作为共产党员而享有社会保障利益的规范是否施加了刑罚的问题上,发生了分歧。相关的最近研究,参见AustinvUS,113SCt2801(1993).在该案件中,对民事没收是否相当于刑罚的情况进行了讨论。这两种不同的解释,最后还是被理解为他们在最初问题上强调的要点不同。第一个解释的焦点主要阐述判断刑事责任是否必须具备行为要件所遇到的难题;第二个解释的焦点是解决判断刑事责任是否具备行为所遇到的困难。纵观该部分的大部分内容,笔者的分析焦点专注于后一种解释中的不确定性(人们对此知之甚少)。刑事责任需要行为要件的论点,很难被解释和适用,这是出人意料的。然而,首先,对前一个解释做出简要的评论,同时对该解释在道德和刑事责任条件对比中所扮演的角色进行简要的评论,这将对问题的论述非常有帮助。
学者对确定刑事责任是否需要行为要件的第一个一般性解释之所以会产生争议,主要在于学者对于行为的性质理解不同。什么是行为?在本章中,笔者交替地使用了“action”和“act”。一些哲学家区分了action和act。例如,参见Eric DArcy,Human Acts(Oxford:Clarendon Press,1963)6-7.哲学家提出了很多不同的概念。可以收集到很多关于行为理论的选集。对于非常有用的刚出版的与行为理论有关的参考书目,参见Jonathan Bennett,The Act Itself (Oxford:Clarendon Press,1995).共识的缺乏增加了关于刑事责任是否需要行为要件的不确定性。根据一种行为的定义,刑事责任是需要行为的,但是根据另一个不同的行为定义,刑事责任可能就无需行为。因此,如果我们不能对行为的概念达成特定的共识,这种争议就会持续。如果是这样,我们就没有理由坚持认为在可预见的未来这个问题会得到很好的解决。
然而,如何解决刑事责任是否需要行为要件这一问题的前景,可能仍然黯淡无光。学者不仅在行为的性质上无法达成一致,而且在确定行为性质应该优先适用何种标准上,也无法达成一致。学者关于这些标准的分歧,在法哲学上是更为广阔、更为基本的具有分歧的问题。这一分歧主要是关于分析哲学与一般法学及具体刑法学的关系问题。正如笔者理解的那样,这一分歧是关于笔者所称的将刑法和道德相融合的趋势的优点与缺点的问题。
那些努力地将刑法和道德哲学相联系的学者,试图找到施加刑事责任的条件,并且主要是通过对各种各样概念进行最具哲学特色的分析手段实现。道德哲学和刑法具有同样的术语。刑法中的部分概念受到道德哲学家的广泛关注,这些概念主要包括行为、意图、因果关系、自愿性、宽恕事由、正当化事由、可谴责性和该当性。法学理论家可能借鉴针对这些概念的哲学分析,来寻找刑事责任的条件。特别是道德哲学家对行为的认定,会被法学理论家援引,从而帮助理解刑法中的行为要件。“在相关的语言社区中的用语,是对这些概念有效性分析的最终标准。”即使“法官或立法者可能……规定或者采用……不符合哲学标准的含义。”参见Nicola Lacey,Contingency,Coherence,and Conceptualism,in R A Duff(ed), Philosophy and Criminal Law(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8)14.当然,刑法会使用特殊的行为概念,这个概念不同于哲学家所解释的行为。但是,为什么要说刑事责任所要求的“行为”的概念,不同于道德哲学家提出的行为概念,而不是承认刑法根本就不需要行为要件?简言之,为什么认为刑事责任所要求的“责任”概念,不同于道德哲学家提出的责任概念,而不是承认刑法根本就不要求责任?
尽管刑法和道德哲学相融合看起来非常合理且有吸引力,但大多数学者抵制将刑法和道德哲学相融合。他们通过区分道德责任和刑事责任,从而认为哲学分析与我们对法律概念的理解并没有特别的联系。对这种立场进行反对的既有哲学家,也有法学家。对使用哲学方法解决社会和政治问题所做出的保留分析,请参见Richard Posners essay “What Are Philosophers Good For?”in his Overcoming Law(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5)444-467.为什么我们要勉强地使用哲学分析来帮助理解法学术语?尽管会得出很多可能的答案当然,经常援引的对此观点进行质疑的观点强调,法律有一系列特定的目的或者目标,这些特定的目的或者目标限制了哲学分析方法的适用。例如,下文中伯纳德·威廉姆斯(Bernard Williams)的评论,就表达了其认为刑罚语境下,不应使用哲学中的与行为相关的概念:
“我们最好还是针对刑法做出一些区分和必要的结论,从而说明我们能够为刑法构建理论。这至少可以说明刑法中的行为理论和行为概念与哲学意义上的行为有所不同。从反思的角度分析,很明显在一些领域中,这种观点是正确的。毕竟,刑法有特殊的目的和目标,并且那些用来描述人行为的要件,不可能与那些独立存在的特殊目的相一致。我们没有理由认为,不需要考虑刑法中的特殊要件,我们使用的各种不同理论和概念就事先已经为刑法准备其所需要的一切东西。”参见Bernard Williams,The Actus Reus of DrCaligari,142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Law Review (1994)1661、1661-1662.
威廉姆斯并没有特殊分析被声称是激励行为哲学家构架他们关于行为理论的特殊功能和目标,他也没有详细认定刑法具有的限制适用哲学分析的“特殊目标、目的和要件”。但是,威廉姆斯认为刑法具有特殊目的和目标的观点,是为大家所熟悉的。,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行为要件在否定将刑法和道德哲学相融合中扮演着核心的角色。更具体分析,在区分道德和刑事责任要件之时,往往会援引行为要件作为理由。刑事责任通常认为必须具备行为要件,而道德责任并不需要行为要件。罗琳·铂金斯(Rollin Perkins)阐述了这一观点,其内容如下:“在伦理学领域,正如教会的教导,罪行仅仅取决于主观心理状态……但是,如果有过错的主观状态并没有产生具有社会危害性的结果,那么就并不存在刑事责任。”Rollin Perkins and Roland Boyce,Criminal Law(Mineola,NY:Foundation Press,3d ed,1982)830.同样的,W赫切尔(W Hitchler)认为:“一项物理行为是责任必备构成要件之一,这就使法律责任与……伦理原则和道德哲学有了区别。对于伦理原则和道德哲学,只要具备主观因素就足以构成罪责。道德规范的表述形式是‘应该是这样’,而不是‘必须这样做’的形式。”W Hitchler,The Physical Element of Crime,39 Dickenson Law Review(1934)96,96.如果该主张是正确的,会被认为是对法律和道德哲学相融合的破坏。
但是,这种主张是否正确?实际上,这种主张涵盖了两种不同的争点:第一个争点是关于刑事责任,并且认为刑事责任的施加必须具备行为要件;第二个争点是关于道德责任,并且认为道德责任的成立不需要行为要件。假设我们认为第一个争点是正确的,即刑事责任的施加必须具备行为要件,那么第二个争点是否就是正确的?道德责任的施加是否就不需要行为要件?如果道德责任的施加也必须具备行为要件,那么这些理论家认为他们已经找到了区分刑事责任和道德责任的标准的观点,就是错误的。
道德责任的施加无需行为要件的主张,通常被鼓吹为一个重要的智慧,因为它揭露了道德和刑法理论的不同结构中最具有深层次意义的重要区别。然而如果我们进一步思考,就会发现该主张最终并非那么有趣,也并没有对刑法和道德哲学的融合产生危害。和刑法评价的范畴相比,没有人会怀疑道德理论有更大的评价范畴。这些例子就是道德哲学家会致力于评价行为、意图、动机、努力、情感、人类、性格、性情和思想,甚至所有可能的世界。一位法学理论家最近提出了这种主张,即:“道德不法的性质,完全取决于行为”,而不是“取决于其他可能的对象”,例如不是取决于动机和意图。然而,如果该学者认为,道德哲学家认为是任何事物的状态而不是行为具有不法性的观点是不合逻辑、荒谬或者是具有误导性的,那么该学者的观点就是错误的。参见Heidi M Hurd,What in the World Is wrong?5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Legal Issues(1994)157、160.很明显,一般的法律和具体的刑法,都不能评价这些多式多样的对象中的每一个。换言之,道德哲学和刑法相比,具有更为广阔的范围。为什么道德哲学的范围和刑法的范围是如此不同,以至于引起了很多困惑,而且这使那些赞成将刑法和道德哲学融合在一起的学者必须进行解释。例如,一个人可为他或者她的性格负道德上的责任,但为什么对性格负刑事责任会被认为不具有正当性而被否决?此外,道德哲学具有更广泛的范畴几乎不会被质疑。当然,行为要件把道德哲学和刑法进行区分,也主要是为了对这种事实进行提醒。
然而,行为是道德进行衡量的对象之一——即使很多类型的不作为,也是道德衡量的对象。道德哲学中,用以衡量行为的部分被称为行为道德。行为道德学派本身(至少)有两派。第一派对行为进行评价的目的是为了事先指导行为。这一派强调的问题是:人们应该实施哪些行为?第二派认为对行为进行评价,是为了事后判断行为。这一派强调的问题是:人们实施的行为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行为道德这两个分支之间的关系,是非常复杂且富有争议的。行为道德和评价其他对象的道德哲学之间的关系是具有争议的。特别是,道德评价的对象可能是主要的和基础的,或者是能被还原为另一种对象的事物,或者是和其他被评价的对象共同处于非常复杂的联系中的事物。这些问题中的一部分问题,已被斯蒂文·哈德逊(Stephen Hudson)讨论过,参见Stephen Hudson,Human Character and Morality:Reflections from the History of Ideas(Boston:Routledge&Kegan; Paul,1986).但是,这些重要的推测并不会挑战这一核心:有一部分道德在评价行为。赫切尔错误地认为“道德规则”必须以“应是这样”的形式进行表达,而不是以“这样做”的形式进行表达。但是,赫切尔是否真的认为,“某人不应该这样做”的形式表达出来的规则,就不可能是道德规则?赫切尔的观点具有颠覆性,而且会产生不为人们所接受的结果——根据刑法做出的判断完全和道德评价无关,因为道德和法律是相互排斥的。
没有行为,就没有评估对象。但在行为道德中,这种必须具备行为要件的主张似乎是多余的。从定义分析,即使欠缺行为要件,道德评价仍然涉及道德哲学中的不同于行为道德的部分。因此,刑事责任必须具备行为要件的主张,至少并不能将刑法与道德哲学中的某些部分区分开。因此,这种观点可能会对刑法与道德哲学中的不会评价行为的部分进行区分,但是,这种观点仅仅注意到不评价行为的道德哲学之部分不需要行为要件,算不上是重要的智慧。即使刑法确实需要行为要件,这一事实也不能把刑事责任所需要的条件从行为道德中区分出来。
尽管笔者也赞同将刑法和道德哲学相融合的一般理论,但在下文中,笔者并不会采用关于行为的形而上学的概念以回答笔者所提出的刑事责任是否需要行为要件之问题。笔者的原因非常简单,任何依赖于具体的关于行为概念的答案,都一定会引起争议正如一个评论家所分析的:“在公共领域,应当尽力避免使用形而上学的行为概念,这不是权宜之计,而是大家所希望的。高度的形而上学,包括行为的形而上学,在一个民主体制中,公民是不会认可的。”参见Samuel Freeman,Criminal Liability and the Duty to Aid the Distressed,142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Law Review(1994)1455,1455.,并且会将注意力从这些实质问题上转向适用该概念的原因之上。回应米歇尔·摩尔(Michael Moore)的研究确定了这种怀疑。值得注意的是,大多数摩尔的批评者都攻击了摩尔的哲学行为论——特别是他的形而上学的现实主义行为观,但对根据摩尔的行为概念,施加刑事责任是否必须具备行为要件却没有多少论述。参见Michael Moore,The Symposium on Act and Crime,142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Law Review(1994)1443-1840.笔者希望最具哲理性的行为论,能够对被证明的问题有帮助,而且能阐明此法律分析之目的。然而,为了回答即将面临的问题,现在我们并不需要对此论点进行阐释。笔者相信,如果对行为的性质缺乏共识,那么就会引起刑事责任是否需要行为要件的分歧。众所周知,哲学上行为概念定义具有不确定性,根据某个令人信奉的行为概念,刑事责任需要行为要件,然而根据另一个被人认可的行为概念,刑事责任不需要行为要件。因此,要判断刑事责任是否需要行为要件,学者就必须在行为的各种概念中做出选择。笔者并不否认存在这种情况。笔者认为通过检验那些理性人都不会有争议的关于是否实施了某项行为的案件,能增进我们对此问题的认识。任何令人信服的哲学上的行为论,都必须符合刑法的最低限制原则。根据此原理,刑事责任必须具备行为要件的论题无论是真是假,都能获得充分的理由。
笔者认为,行为本质的形式主义的困惑,仅仅是行为要件持续具有争议的部分原因。在这一部分的论述中,笔者将特别关注那些相对而言还不为人知的争议——刑事责任是否需要行为要件争议到底意味着什么的不确定性所导致的争议。笔者认为学者对于行为本质的理解还有所欠缺,正是这种模糊性概念选择才导致对刑事责任是否需要行为要件的判断出现分歧。
……
前言/序言
在一定的限制条件下,由已发表的论文集成专著是非常有价值的,至少本专著就是如此。笔者的这本专著就是由笔者以前发表的诸多均匀分布在哲学期刊、法律评论和书籍中的章节组成。其中,很多文章已引起法学教授们的注意,还有很大部分的文章则已为哲学家所熟知。笔者通过非正式调查得出结论:在笔者所著述的论文中,诸多学术研究的学者们几乎只是对笔者的立场或观点略知一二而已。笔者希望该专著的读者能更加熟悉笔者的一些文章的内容,这亦将有助于他们全面了解笔者的观点和立场。事实上,这些分布在不同领域的文章反映了笔者对刑法理论的性质与功能的一些独特观点,这亦是笔者在该导言中强调的主题。笔者将努力简略阐述笔者的立场以及在相关作品中说明的学术观点。但是,要简要阐述笔者的学术观点,事实上是非常困难的,因为笔者提出的大多数观点需要直接的条件:一方面笔者认同X,但另一方面,笔者也亦认为不应该忘记Y。但是,在此,笔者提出一个相对比较谦和的开端:刑法哲学(或刑法理论)的目标,正如笔者所诠释的,是提出建议从而去改善刑事实体法的内容。当然,这个粗糙的界定亦会引起诸多问题。除此之外,我们还需要拟定一个标准,以便于判断某种理论是否能促进刑法的发展。笔者主要用道德哲学(另外,笔者也会从社会和政治哲学的视角进行分析)来界定该标准。然而,道德哲学家对规范性问题的分析,其观点亦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据此,我们应援引何种传统道德观评价刑法?在大多数情况下,笔者试图回避这个问题。然则,不管是好是坏,笔者在导言中提出的诸多观点,几乎不涉及任何道德理论。
因此,笔者不打算构建宏观理论,亦即,笔者并非寻求关于刑法目的的统一理论。虽然笔者时常从抽象转移至具体,但笔者更倾向于拒绝一般性的某种主义,即最为大家熟知的具体性的某种主义。笔者认为,我们应该在刑法理论中避免涉及意识形态。在笔者的著述中,笔者没有使用“自由主义”或者“保守主义”这些术语。笔者认为继续使用这些模糊的标签性术语对政治和法律争论是没有益处的,而笔者期望提出的观点能对整个政治领域的问题都有裨益。笔者期望各种意识形态下的人都能从笔者的著述中获得启发。
笔者不愿意讨论各种法律主义或者对某个基本问题表明立场,这会令那些甚至对综合性道德理论都没有印象的哲学家们感到失望,而正是综合性道德理论使这些哲学家的理论具有正当性。然而,笔者担心提出这种统一的理论框架不会增加多大益处。任何反对提出理论根基的学者,都会对理论根基上的理论建设表示怀疑。笔者希望笔者提出的假设和从中得出的推论,能与那些不同意更深层次地探讨理论根基问题的哲学家们的主张一致。笔者在该书使用的方法论,与最著名的法律哲学家乔尔·范伯格(JoelFeinberg)的方法论最为相似。笔者有意识地引用了范伯格所偏爱的“中级审查标准”。在论述风格和实质内容两方面,范伯格对笔者影响很大,那些熟悉其著述的学者应该非常清楚其对笔者的影响。
尽管笔者避免讨论道德理论中的大多数具有争议的问题,但是笔者认为构成刑法基础的道德和一般道德哲学之间存在非常紧密的联系。尽管笔者认为这种联系是紧密的,但是与把笔者的刑法理论归纳为几个简单的原则相比,把道德理论归结为几个原则更不具有可能性。道德的内容体系更具有争议且更加复杂,因此,笔者对不能成功地构建统一的道德理论体系并无歉意。任何道德基本问题,都将引起道德哲学家的争鸣,我们也期望这些争鸣出现在刑事实体法领域中。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刑事理论法学家,都认为构成刑法的道德基础是复杂的。例如,最近一些著名的学者认为所有的刑事不法行为都可以简单地解释为:不具有充分合理性,选择了可能给他人或他人的利益带来危害风险的行为。参见LarryAlexander、KimberlyKesslerFerzan、StephenPMorse,CrimeandCulpability:ATheoryofCriminalLaw(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2009)。笔者认为该简单的原则过于简化了(并且扭曲了)刑法。该导言的目的不是批评其他学者的不同观点。因此,笔者只能简单地阐述,在笔者所支持的简化原则中,没有任何原则像上述简化原则那样。
虽然刑法理论和道德理论是紧密联系的,但是二者可能在一些有趣的方面产生分歧。当代道德哲学家之间的关于行为人之目的是否与评价行为人的行为是否具有容许性的争鸣就是这种情况。无论道德哲学家的观点如何,笔者在第三章“刑法语境下‘目的不影响允许性’假定论的代价”中分析认为,证明目的与行为人是否实施犯罪行为无关紧要,将产生很多误导,并且会带来潜在的灾难。笔者认为刑事实体法应该坚持目的对评价行为人的行为是否被允许具有重要意义。在第十四章“刑事责任中‘轻微违反’辩护事由”中,笔者探究了其他可能在刑法和道德之间产生的分歧。在道德中,非常微小的错误行为都是可以被认知的,而且会使人受到较小程度的谴责。但是在刑法中,情况则与之形成鲜明对比,非常轻微的犯罪行为根本不会使被告受到刑事惩罚。如果笔者的观点是正确的,那么正当化事由这个概念在法律与道德中的含义是不同的。为了达到施加刑事责任之目的,正当化事由不需要完全排除行为之不法性。正当化事由只需要排除足够的不法性,从而使被告不承受报应之谴责。这就是笔者大致的观点。
笔者对道德理论中的一个基本问题持有坚定的立场:构成刑法基础的道德,是且应该完全是道德性的。笔者断然否定这样的观点:刑事司法的各项制度,包括拟定的法律、政策和原则等,都当且仅当能使利益最大化时才能被采纳。一些提案虽然能实现利益的最大化,但是不应该以法律的形式实施,其他的一些提案虽然不能实现利益的最大化,但却应以法律的形式执行。在笔者的这本书中,读者几乎找不到结果主义的推理线索。更具体分析,虽然有学者通过评价规则或原理的威慑效果来评价规则和原理,但笔者一直拒绝该众所周知的评价倾向。首先,具体的法律原则增强或降低刑法作为威慑工具之效果具有一定的条件,但在现实世界中,我们能满足这样条件的情况很少。笔者论证的上述问题需要的条件,在我们大多数公民中是缺乏的,并且如果公民不能认识到这些法律,并据此调整他们的行为,那么提案就不会影响公民的守法程度。此外更重要的是,威慑和刑法理论中最基本的公正与该当性概念并无关系。当刑事司法违反道德约束并偏离公正与该当性时,刑事司法制度就是被滥用了。尽管许多学者习惯于认为并期望刑法能在保护被告人权利和维护社会利益之间维持微妙的平衡,但在笔者的这本书中,似乎没有特别关注对社会的保护。然而事实上,笔者同意刑法应具有阻止犯罪的功能。在判断何种行为应该受到刑事处罚时,我们是在判断我们应阻止何种行为。当然,这种判断所关注的焦点仍然是公正和该当性。
如果没有争议,则如何实现笔者讨论的理论的发展?如果不经常对具有争议的理论问题进行思想上的交锋,那么对研究的规范性问题是没人能得出结论的。笔者在书中提出的一些假设的案例,主要是为了征求读者的意见。在反思平衡的过程中,读者的回应可以用于确认或反对抽象的原则或理论。这种方法论基本上是不可避免的,笔者在本书中偶尔会使用。但是,笔者会避免广泛列举这种充满想象的假设案例,因为在法学领域并不推崇使用太多的假设案例进行研究。读者对这些特殊案例的回应,不具有体系性效应,而且还存在其他的心理歪曲的情况。因此,笔者对这些案例的可信度表示怀疑。在刑法发展的历史上,产生过数量巨大的案件。如果道德哲学家对现实案例熟悉,那么就没有必要设计假设的案例。
当然,笔者认为道德性和以该当性为基础的分析视角,在刑法学界还没有得到普遍认同。据笔者分析,目前刑法学家研究的主流趋势是实证主义。这种研究方法主要是依赖于社会科学,而不是依赖于一般哲学或具体的道德哲学。对此种现象笔者是矛盾的。一方面,刑法理论的研究应该是广泛的,应该接受不同的研究方法,当然也不应排除实证主义方法。因此,对于最近许多刑法哲学家愿意参与到实证研究中,笔者表示赞同。但另一方面,道德争议是不能通过民意调查来解决的,因为民意调查反映的是回应者思考的是什么,并且我们应该不让实证调查把我们从辛辛苦苦维护的规范性结论中分离出来。同时,笔者亦相信公众意见体现的智慧比刑法学者想象得要高。最近几年,甚至有学者已经调查出外行人是如何看待刑法学说的。基于很多原因,这些学者甚至认为公众的正义观,应该反映在刑法实践中。在这些原因中,至少包括能增强对刑事司法制度之公正的信心,从而加强自愿守法。
笔者基于不同的原因从社会学中寻找数据。例如,令笔者感到震惊的是:刑事实体法中什么程度的宽恕事由才能成为部分或完整的宽恕事由,与被指控犯罪的行为人在请求中提出的部分或完整的宽恕事由的程度差异很大。社会规范在确定宽恕事由之决定因素中的作用很大。研究侵权行为的学者时常指出,理性人不属于统计学上的普通人。这些学者的观点是正确的,但是在刑事法领域,该问题就不那么容易回答了。如果施加刑事责任表达的是一种谴责,当然笔者也持这种观点,那么行为人遵守广泛社会规范的事实就有力地证明行为人不应受到惩罚。“但每个人都这样做”之辩护事由,通常都缺乏事实根据。但是,如果被告的请求从经验分析完全是正确的,那么就很难理解被告为什么应该承受刑法施加的污名效应。
此外,法律制度之外追求的社会实践可能比刑法哲学家所思考的社会实践更具有意义。尽管刑法哲学家对于刑罚的本质分歧很大(令大家更熟悉的是这些刑法哲学家对刑罚正当性之分歧),许多学者坚持认为这个意义上的刑事制裁,仅仅只是国家的行为,其旨在使实施了犯罪的行为人承受剥夺权利和污名效应之痛苦。在该书的第十七章“‘已受足够惩罚’辩护事由”部分的论述中,笔者认为企图因犯罪人之犯罪而惩罚犯罪人之个人的反应,可以减轻国家施加的正当刑事制裁。如果笔者是正确的,刑事政策就应该更敏感地捕捉公众对被告的态度。特别是,当公众对那些名人进行谴责,从而使其受到更多的污名痛苦时,他们就可能受到较轻的刑罚。
尽管社会学家在法律哲学中扮演了一定的角色,但是笔者担心最近流行的实证主义趋势会使刑法学者不能成功培养接受以该当性为基础的方法论的新一代学者。在美国,许多很好的法学院都没有聘请赞同笔者在该书提倡的规范框架的全职教员。然而,该规范框架是非常有价值的,笔者也非常相信确实如此。但是,笔者担心能应用这个方法的年轻学者是相对缺乏的。许多教授刑法的学者不接受义务论式刑法理论,更愿意从公诉人或是辩护律师的职业角度教学。笔者和笔者的同事们会因没有成功培养出以该当性为基本观点的新一代年轻学者而感到遗憾。笔者只希望本书的理论和最近由约翰·加德纳(JohnGardner)编写的优秀论文集能起到更大的刺激兴趣的作用。参见JohnGardner,OffencesandDefences(Oxford:OxfordUniversityPress,2008)。
引起更多的兴趣是必要的。正如笔者所解释的那样,学术界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忽视刑法理论,但笔者提出的义务道德思想和刑法理论的关系可以解释这种忽视。许多不同的学派的学者遭受了笔者所称的道德论之恐惧:如果某问题的解决有赖于道德争论的解决,那么该问题自然不能得到解决。因此,研究刑法的普遍方法大部分都是借助于社会科学,并且期望借此弄清楚道德正义,这不足为奇。对道德学说的厌恶,使一些学者否认刑法应该被道德约束。许多认为道德是刑法之基础的学者,认为道德结果主义,关于正义与该当性的争论,会使问题变得更难以解决,而且不会取得进步。从抽象角度很难解释道德争论恐惧症。参与道德争论是厌恶道德争论学者的最好解药,而笔者在该书中亦试图这样做。
正如笔者所解释的,刑法理论被忽视具有诸多不同的原因。也许,学者也确信其所作的理论工作不会有积极的成效。笔者熟悉的许多刑法学者,都感叹他们的理论工作对现实世界没有影响力。在我们这些理论学者中,极少有人会认为法学家的著述会对现实世界的政策有实质影响。众所周知,政治家和公众都希望“严厉打击犯罪”,并且普遍抵制使我们的刑罚制度更符合正义和该当性要求。从2008年开始的经济严重衰退,可能会改善这种可怕的情况。因为让一个犯人待在监狱每天要花费80美元,这使那些有着最严厉名声的司法管辖区,也被迫从严厉压制犯罪的实践中撤退。笔者推测我们刑事惩罚机构的改革,不是因为法学家的请求而是因为最近紧张的刑事司法预算。当我们对道德置若罔闻时,经济上的考虑就会占优势。经济考量具有重要意义的这一变化,实质上与刑法理论学者的主张相契合。我们不应该放弃这个机会,向那些愿意接受真正改革的政策制订者们提出建议。如果我们不能明确地知道我们能提出什么建议,那么我们就不能抱怨现实世界对刑法学者的忽视。我们必须准备如何向当局提出更好的修改立法的建议。尽管笔者非常清醒地知道,对于如何鼓励政策制订者实施笔者的建议亦没有很好的建议,但是很显然,鼓励政策制订者接受刑法学者的建议,对于改善刑事实体法至关重要。
笔者之道德构成刑法之基础的观点,对于参与刑事司法日常工作的人而言,可能是不能接受的。现在的刑事司法被称为McJustice模式,该模式使近95%的案件是通过与被告人进行匆忙的谈判,从而让其认罪的方式而结案的。NewYorkTimes,11September2008A1:1。负担过重的公诉人和极度超负荷工作的公共辩护人,都参与到辩诉交易制度这个生产线中。刑事实体法中的任何改革,都不可能帮助司法实践者在这种被歪曲的司法制度中有效地扮演好自己的角色。然而,正如许多学者所指出的,如果极少有人自我认罪,案件也不是通过辩诉交易进行,那么我们的刑事司法体系就会崩溃。尽管笔者在该书中提出的解决方案不多,但笔者呼吁犯罪学家和社会学家能够关注这个糟糕的现状,并且提出一些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
专门从事刑事理论研究的法学家主要分为两大派别。一派主要是学术型法学家,这些法学家非常精通道德责任和政治责任,并且努力把其见解应用到刑事责任理论中。这些法学家可能写了很多刑法专著,但几乎没有提及一个案例或法条。另一派是法学教授,这些法学教授知道大量的规范和案例,但是却不熟悉法哲学。这类学者对哲学的精通程度,仅限于如何使其观点在威慑和报应的传统中被接受而适用的哲学程度。当然,一些法学哲学家处于这两个极端中。笔者将自己界定在这两个学派之间。笔者坚定地以现行刑法为基础,从当代道德、政治和社会哲学中吸收大量经验。与之同时,笔者偶尔也会借鉴犯罪学家的实证研究。笔者希望通过努力,领悟这些学科中最好的内容。笔者一直希望笔者的著述,对于法学家而言不要太哲学化,对哲学家而言不要太法律化。读者既不必要是哲学博士,亦不必要是法学博士,就可以理解和评价笔者本书所写的内容。
尽管笔者的研究方法是比较均衡地借助了哲学和法学的方法,但笔者并不认为任何派别都可以借助此路径在刑法理论研究中处于垄断地位。虽然似乎显得很奇怪,但任何一个法律哲学家即使较少关注现行法律,也能做出很大成就。该情形让我们回忆起60年代哲学科学的状态。在那个时代,尽管许多学者对科学知之甚少,但许多著名的学者都试图对科学哲学化。然而,对法理学领域广受欢迎的原则和概念的关注,导致对现行法律规则和学说关注的缺失。例如,假设认为法哲学应该探究法律的必然真理,尽管后来学者把此概念视为法理学,但法律之真理的概念却在约瑟夫·拉兹(JosephRaz)的著作中能找到。参见JosephRaz,TheAuthorityofLaw:EssaysonLawandMorality(Oxford:ClarendonPress,1979)104-105。那么根据理念,现行法律的规定是如此严格,导致其几乎不可能赢得法哲学家的关注。即使该理念在法学领域貌似有理——笔者对此深表怀疑——但笔者在该书中也不会采取这种研究路径。笔者不会寻找所有刑法体系的共同特征,相反,笔者会均衡地从现行法律和哲学中寻求方法。
用户评价
《刑法哲学》这本书的阅读体验,可以用“耳目一新”来形容。它并非是一本堆砌理论的著作,而是充满了作者独到的见解和深刻的洞察。我非常欣赏作者对“犯罪原因”的探讨,他不仅仅停留在社会学和心理学的层面,更是将哲学思考融入其中,去探究那些导致个体走向犯罪深层的根源。书中对于“犯罪构成要件”的分析,也异常精辟,它不仅讲解了客观和主观方面的要件,更重要的是揭示了每一个要件背后所蕴含的价值判断和法律精神。这让我意识到,刑法并非是冷冰冰的规则,而是承载着社会对行为的期望和对个体的要求。这本书的语言风格也十分吸引人,它既有学术的严谨,又不失文学的色彩,读起来流畅且引人入胜,仿佛在跟随作者一起解剖一个复杂的犯罪案件,并从中窥探到法律背后那深邃的智慧与人文关怀。
评分坦白讲,《刑法哲学》这本书的阅读体验非常独特,它不像我之前读过的任何一本法学著作。作者的语言风格非常有趣,有时犀利,有时幽默,但始终保持着一种严谨的学术态度。我特别喜欢他对“免责事由”的分析,比如正当防卫、紧急避险等,他不仅仅是在解释这些概念,而是将它们置于更广阔的哲学背景下,探讨个体在面对威胁时,其行为的“正当性”是如何被法律所承认的。这让我联想到很多现实生活中的案例,有时候我们会觉得某人的行为是出于无奈,但法律是否也同样理解和包容?书中对于“故意”和“过失”的区分,也进行了极其细致的论证,它不仅仅是关于行为的主观意图,更是涉及到了对风险的预见能力以及行为人所应承担的注意义务。这种深入的剖析,让我对刑法的精妙之处有了全新的认识,也看到了法律背后对人性复杂性的深刻洞察。
评分这本《刑法哲学》读起来真是让人眼前一亮,完全颠覆了我之前对刑法枯燥、冰冷印象。作者的笔触非常细腻,不像一般的学术著作那样生涩难懂,而是像在娓娓道来一个关于正义、惩罚和罪责的故事。我尤其喜欢其中关于“应报”理论的探讨,它不仅仅是简单地罗列各种观点,而是通过大量生动的案例和哲学思辨,层层剥开应报的复杂性,让我们思考,当法律的惩罚不仅仅是威慑,更是对被剥夺之物的某种“补偿”时,这种补偿的真正意义何在?它是否真的能带来一种秩序的恢复,或者仅仅是一种情绪的宣泄?读到这里,我仿佛置身于古希腊的广场,与智者们辩论着“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合理性,又或是身处现代的法庭,审视着量刑的尺度是否真正体现了“罪责刑相适应”的原则。书中的很多观点都非常有启发性,它迫使我去重新审视自己对犯罪和惩罚的理解,不再是简单的好人坏人二元对立,而是看到了法律背后更深层次的伦理考量和社会功能。
评分我必须说,《刑法哲学》这本书带给我的冲击远超预期。我原本以为它会是一本充斥着法条和案例的“工具书”,没想到却是一场思维的盛宴。作者的逻辑构建异常清晰,他从最基础的“什么是刑法”开始,一步步引申到刑法的目的、功能,以及它与社会伦理、道德之间的微妙关系。尤其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关于“预防”理论的论述,它不仅区分了“一般预防”和“特殊预防”,还深入探讨了它们各自的局限性和潜在的风险。比如,为了达到“威慑”的目的,刑法的严厉程度是否会走向极端?而“特殊预防”在改造罪犯的过程中,又是否会触及个体的自由和尊严?这些问题都让我陷入了深深的思考,也让我对法律的制定和执行有了更深刻的认识。这本书不是那种读完就忘的书,它更像是一把钥匙,打开了我对刑法背后复杂社会机制的理解之门,让我看到了法律是如何在维护社会秩序的同时,又必须时刻警惕自身可能产生的负面效应。
评分对于《刑法哲学》这本书,我只能用“震撼”来形容我的感受。它不是简单地介绍刑法条文,而是带领读者进行一场深刻的哲学之旅。作者以一种非常宏大的视角,审视了刑法的起源、演变及其在现代社会中的地位。我尤其被关于“刑罚的功利性”与“刑罚的惩罚性”的辩论所吸引。究竟刑罚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改造社会、预防犯罪,还是仅仅为了对罪犯施加惩罚以体现正义?这两种看似对立的理念,在实际的法律实践中是如何交织和冲突的?书中的论证过程非常精彩,它引用了大量的思想家观点,并将其与具体的法律条文相结合,让我看到了刑法理论的深邃之处。读这本书,感觉像是在与一位饱学之士进行思想的对话,每一页都充满了智慧的火花,让我对法律的理解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也对社会公正的实现有了更深刻的反思。
评分理论性东西,还不错?
评分经常在京东买书,质量值得信赖
评分很棒的刑法著作!
评分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好好
评分挺好的,留着慢慢看~
评分东西不错,京东品质,值得信赖。
评分挺好的,留着慢慢看~
评分非常好好好!!!!!!
评分特别好特别好特别好好好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内容均为互联网搜索引擎提供的公开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储任何数据与内容,任何内容与数据均与本站无关,如有需要请联系相关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于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6 book.cndgn.com All Rights Reserved. 新城书站 版权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