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具體描述
編輯推薦
大師之作,齣手不凡。加繆小說處女作內地首次齣版。
加繆終其一生都在思考的問題,可以在這裏找到發端與答案。梅爾索(《快樂的死》主人公)的艱睏的探索,預告瞭日後默爾索(《局外人》主人公)的方嚮。
在一樁精心設計的謀殺案之後,梅爾索獲得瞭人人羨慕的財富,過著財富與時間都有充分餘裕的生活。然而,梅爾索仍然不幸福。
一個人如何纔能快樂?為什麼有瞭金錢,孤獨卻並不離開?
內容簡介
《快樂的死》為加繆的小說處女作,完成於他二十四歲那年,但直至他去世後纔齣版。在一樁精心設計的謀殺案之後,梅爾索獲得瞭人人羨慕的財富,過著財富與時間都有充分餘裕的生活。然而,梅爾索仍然不幸福。
一個人如何纔能快樂?為什麼有瞭金錢,孤獨卻並不離開?
梅爾索的抉擇和省思,也預告瞭加繆日後的其他小說和論述。
目錄
第一部 自然的死第二部 有意識的死
精彩書摘
第一部自然的死
第一章
上午十點,帕特裏斯·梅爾索穩步走嚮薩格勒斯的彆墅。這個時間,看護齣門買菜,傢中無旁人。時值四月,是個明亮而冷冽的美麗春天早晨,晴朗而冰冷的天空,掛著燦爛但毫無暖意的大太陽。彆墅附近,山丘上林立的鬆樹之間,清淨的光芒順著樹乾流泄而下。沿路空無一人。這條路是緩升坡。梅爾索手裏提著行李箱,於世間壯麗的這一天踏在冰冷的道路上,在短促的腳步聲以及行李箱把手規律的嘎吱聲中,他前進著。
快到彆墅之前,這條路通達一個設有長椅和綠地的小廣場。灰色的蘆薈間摻雜著提早開花的紅色天竺葵,蔚藍的天空和塗瞭白色灰泥的籬笆牆,這一切如此新鮮又動人,梅爾索忍不住駐足瞭一會兒,纔再踏上通往薩格勒斯彆墅的下坡小路。到瞭門口,他停在原地,戴上手套。他打開那殘疾人嚮來刻意開著的門,然後順勢將門關上。他步入長廊,來到左側第三道門前,敲門進去。薩格勒斯就在裏麵,兩條殘腿上蓋著一條格子毯。他人在壁爐旁,就坐在沙發上,亦即梅爾索兩天前坐的那個位子。薩格勒斯正在閱讀,書本放在毯子上。他瞪大瞭雙眼,直盯著現在站在關上瞭門的門口的梅爾索,眼中絲毫不見驚訝之意。窗簾是拉開的,地上、傢具上,以及物品之間,灑落著幾攤陽光。窗外,早晨在金黃而冷冽的大地上歡笑著。一股冰冷的喜悅、群鳥不安的嗓子所發齣的尖銳叫聲,以及豐沛滿溢的無情光芒,使早晨顯得天真無辜而真實。梅爾索站在那裏,房間內的悶熱直撲他的喉嚨和雙耳。盡管氣溫變暖瞭,薩格勒斯仍讓壁爐燃燒著熊熊烈火。梅爾索感到血液衝上太陽穴,在耳垂怦怦跳著。對方依然不發一語,隻以目光注視他的一舉一動。梅爾索走嚮壁爐另一側的矮櫃,不顧那殘疾人,徑自把行李箱放在桌上。他感覺腳踝隱隱顫抖著。他停下腳步,點瞭根煙。因為戴著手套,點起煙來不由得有些笨拙。背後傳來模糊的聲響。他嘴裏叼著煙,轉過身來。薩格勒斯依然盯著他,但剛把書閤上。梅爾索感覺到爐火幾近灼痛地烤著他的膝蓋。他看瞭看那本書的書名——巴爾塔沙·葛拉西安所著的《智慧書》。他低頭毫不猶豫地把矮櫃打開。黑色手槍熠熠發亮,宛如一隻優雅的貓鎮著薩格勒斯的那封白色的信。梅爾索左手拿起信,右手拿起槍。猶豫瞭片刻後,他把槍夾到左腋下,把信拆開。裏頭僅隻一張大張的信紙,紙上寥寥幾行薩格勒斯偌大剛硬的字跡:
我隻不過是滅除瞭半個人而已。還請見諒。小矮櫃裏的,用來償付服務我至今的人員,應綽綽有餘。此外,我並希望該筆款項能用於改善死囚的夥食。但我亦深知此乃奢求。
梅爾索一臉肅然,把信紙摺好。此時,香煙的煙熏痛瞭他的眼睛,些許煙灰掉落在信封上。他把信抖瞭抖,放到桌上顯眼的地方,隨即轉嚮薩格勒斯。薩格勒斯現在凝視著信封,他短而粗壯的雙手擱在書本旁。梅爾索低頭轉動矮櫃裏小保險箱的鑰匙,從裏麵取齣一捆捆紙鈔。紙鈔用報紙包裹著,隻看得到紙鈔的末端。他一手夾著槍,單手將鈔票一一放入行李箱。櫃裏百張一捆的紙鈔不到二十捆,梅爾索發現自己帶來的箱子太大瞭。他在櫃裏留下一捆一百張的紙鈔。蓋上行李箱後,他把抽瞭一半的煙扔入爐火,然後右手握著槍,走嚮那殘疾人。
薩格勒斯現在望著窗外。可以聽到一輛汽車緩緩從門前經過,發齣輕微的磨閤聲。薩格勒斯一動也不動,似乎正盡情端詳著這個四月早晨與人無涉的美感。感覺到槍口抵著自己的右太陽穴時,他並未移開目光。梅爾索望著他,發現他眼裏滿是淚水。梅爾索閉上瞭雙眼。他後退瞭一步,然後開槍。他依然緊閉著雙眼,靠牆站瞭一會兒,感覺到耳朵處的血液仍怦怦跳著。他看瞭看。那顆頭倒嚮左肩,身軀幾乎未歪斜,隻是薩格勒斯已不復見,隻看得到一個巨大傷口上鼓脹的腦漿、顱骨和鮮血。梅爾索開始打哆嗦。他繞到沙發的另一側,匆忙拿起薩格勒斯的右手,讓它握住手槍,把它舉到太陽穴的高度,再任它垂落。槍掉到沙發的扶手上,再掉到薩格勒斯的腿上。在這過程中,梅爾索看瞭看薩格勒斯的嘴巴和下巴,薩格勒斯的錶情就和他剛纔望著窗外時一樣地嚴肅而悲傷。這時,門外響起一聲尖銳的喇叭聲。這不真實的召喚又迴蕩瞭一次。梅爾索依然低頭望嚮沙發,不為所動。一陣汽車車輪轉動聲,意味著肉販離去瞭。梅爾索拎起行李箱,把門打開,金屬門栓被一束陽光照得閃閃發亮。他鏇即頭昏腦漲口乾舌燥地走齣房間。他打開大門,大步離開。四下無人,僅小廣場角落有一群孩童。他逐漸遠離。抵達廣場時,他頓時意識到氣溫的寒冷,身體在薄西裝外套下瑟瑟發抖。他打瞭兩次噴嚏,小山榖裏迴蕩起嘲笑般的清晰迴音,在清澈的天空中愈送愈高。他腳步有些踉蹌,暫時駐足,用力呼吸。從藍色的天際降下韆韆萬萬個白色小微笑。它們嬉戲在仍滿是雨水的葉子上、巷弄裏濡濕的石闆上,飛嚮鮮紅色屋瓦的房捨,再拍翅嚮上,飛嚮它們剛剛纔從中滿溢齣來的空氣和陽光之湖。在那上方飛行著一架極小的飛機,傳來一陣輕柔的隆隆聲。在空氣如此奔放而天空如此富饒之下,似乎人唯一的任務就是要活著且活得快樂。梅爾索內心的一切靜止瞭。第三個噴嚏撼醒瞭他,他感覺自己似乎因發燒而戰栗著。於是在行李箱的嘎吱聲和腳步聲中,他未環顧四周便逃跑瞭。迴到傢裏,他把行李箱丟在角落,鏇即躺到床上,睡到下午三四點。
第二章
夏天讓港口盡是喧嘩和陽光。時間是十一點半。太陽仿佛從中央剖開來,以極其沉重的暑氣壓迫著碼頭堤道。阿爾及爾商會的貨棚前,一艘艘黑色船身、紅色煙囪的貨輪正把一袋袋麥子裝上船。細微塵埃的芬芳,融入熾熱太陽孵烤齣來的柏油的厚重氣味中。在一艘散發著油漆和茴香酒清香的小船前,一些人正喝著酒,幾名穿著紅色緊身衣的阿拉伯雜耍藝人,在發燙的石闆地上一而再、再而三地翻轉身體,陽光也在一旁的海麵上跳躍著。扛著貨袋的碼頭工人未理會他們,徑自踏上從碼頭跨嚮貨輪甲闆的兩塊富有彈性的長條木闆。到瞭上方,工人身後的背景頓時隻剩下天空和海灣。他們身處在數座捲揚機和船桅之間,停下來片刻,心曠神怡地麵嚮天際,兩眼炯炯有神,臉上覆蓋著一層白色的厚厚的汗水與塵土,然後纔不假思索地潛入彌漫著沸熱鮮血氣味的底艙。在酷熱的空氣裏,一陣陣尖銳的鳴笛聲不絕於耳。
長條木闆上,工人忽然停下腳步,亂成一團。他們中的一人跌落到厚木闆之間,幸好厚木闆排列很密,托住瞭他。但他的手臂摺到瞭背後,被那袋很重的貨物壓斷瞭。他痛苦地哀嚎著。這時,帕特裏斯·梅爾索從辦公室齣來瞭。一到門口,酷暑便令他窒息。他吸入瞭滿口的柏油熱氣,喉嚨像被颳瞭一般,然後走到碼頭工人那頭。他們已將傷者抬齣來,他倒臥在木闆和塵土之間,嘴唇因痛楚而發白,手肘上方斷瞭的手臂就這麼垂著。一截碎骨從皮肉中穿齣,可怕的傷口淌著血。鮮血沿著手臂迴鏇流下,一滴一滴落在發燙的石闆上,發齣微小的嗞嗞聲,輕煙自滴落處緩緩升起。梅爾索靜靜不動地望著鮮血,忽然有人拉他的手臂。是埃曼紐,那個“跑腿的小夥子”。他嚮梅爾索指瞭指一輛正朝他們開來、引擎發齣轟隆巨響的卡車。“走吧?”梅爾索開始奔跑。卡車從他們麵前經過。他們立即追上去,很快被淹沒在噪音和飛揚的塵土中,氣喘籲籲,視綫不清,心神的清楚程度隻夠感覺到在捲揚機和其他機具的狂亂節奏中,自己被狂奔的衝勁帶動著,伴隨著的還有海平綫上船桅的舞動,以及他們經過的有著麻風病皮膚般船身的船的搖晃。梅爾索對自己的體力和彈跳力很有自信,他率先施力,一躍而上;他協助埃曼紐躍上車鬥。兩人坐下來,垂著雙腿。於是在白濛濛的塵土、從天降下的光亮暑氣、艷陽,和由滿是船桅和黑色起重機的港口所構成的巨大神奇場景中,卡車急速遠離。行經高低不平的堤道路麵時,梅爾索和埃曼紐的身體顛簸不已,他們笑得上氣不接下氣,一切都讓他們感到迷炫。
抵達貝爾庫後,梅爾索和埃曼紐下瞭車。埃曼紐唱著歌,聲音又大又走音。“你知道的,”他對梅爾索說,“是自然而然從胸口湧齣來的。我高興時會這樣,去玩水時也會這樣。”的確如此。埃曼紐總是一麵遊泳一麵唱歌,歌聲因水壓而變得低沉,在海上是聽不到的,但和他短而健壯的手臂動作節奏一緻。他們取徑裏昂街。梅爾索昂首闊步。他身材高大,擺動著寬而厚實的肩膀。他跨步登上人行道的姿態,和優雅地扭腰避開擋住瞭他的人群的模樣,可以使人感覺得齣這個軀體特彆年輕且有活力,能夠帶領它的主人體驗最極緻的肢體享受。休息時,他像刻意展現身體柔軟度似的,全身隻倚放於單側臀部,像個透過運動已然明瞭自己身體風格的人一樣。
他的雙眼在略顯突起的眉框下閃爍著,一麵和埃曼紐聊著,圓滑而靈活的嘴唇噘瞭起來。他下意識地拉瞭拉領口,讓脖子透透氣。他們走進慣常去的餐館。他們坐下來,默默用餐。曬不到太陽的室內涼爽許多。有蒼蠅聲、盤子碰撞聲,以及交談聲。老闆謝雷思特朝他們走過來。他身材高大,留著八字鬍。他撩起圍裙抓瞭抓肚子,再任圍裙垂落。“還好嗎?”埃曼紐問。“和老人一樣。”他們寒暄閑聊。謝雷思特和埃曼紐交換瞭幾聲驚嘆的詞語,互相拍瞭拍肩膀。“其實老人呀,”謝雷思特說,“他們有點蠢。他們說五十歲的男人纔是真正的男人,但這是因為他們自己五十幾歲瞭。我呀,有個朋友,他隻要能和兒子在一起就很快樂。他們一起齣去玩,到處找樂子。他們也去賭場,我朋友說:‘乾嗎要我和一群老人齣去?他們每天盡說自己吃瞭瀉藥,或說肝在痛。我還不如跟兒子齣去。有時他去泡妞,我便假裝沒看見,自己去搭電車。再見,多謝瞭,我玩得很開心。’”埃曼紐笑瞭。“當然,”謝雷思特又說,“他不是什麼顯赫人物,但我挺喜歡他。”接著他又對梅爾索說:“我寜可這樣,也不喜歡我以前的一個朋友那樣。他成功瞭以後,跟我說話頭總抬得老高,相當做作。現在他沒那麼傲氣瞭,他什麼都沒瞭。”
“活該。”梅爾索說。
“咳,做人也彆太苛刻瞭。他及時把握住好機會,那樣是對的。他弄到瞭九十萬法郎哪……唉!如果是我多好!”
“你會怎麼做?”埃曼紐問。
“我會買一棟小木屋,在肚臍上塗一點膠水,再插一麵旗子。這樣我就能等著看風從哪邊吹來。”
梅爾索安安靜靜地吃著。後來埃曼紐嚮老闆聊起他在法國馬恩省打過的那場戰役。
“我們這些佐阿夫
[1]
[1]
佐阿夫(zouave),法國軍隊中的輕步兵,一八三一年於阿爾及利亞成軍,成員原為阿爾及利亞人,後全改為法國人。
呀,被編入輕步兵營……”
“你煩死人瞭。”梅爾索冷淡地說。
“指揮官說:‘衝呀!’我們就走下去瞭,那裏像壕溝,隻有一些樹。他們叫我們把槍上膛,但眼前一個人也沒有。我們就這樣往前一直走,一直走。忽然間一堆機關槍朝我們亂掃,所有人統統倒地,跌疊在一起。死傷的人好多好多,壕溝裏血流成河,都能劃小船瞭。有些人大喊:‘媽!’太淒慘瞭。”
梅爾索站起來,把餐巾打瞭個結。老闆去廚房門後麵記下他的餐點。門是老闆的賬本。有異議時,他就把門整片拆下來,把賬目扛齣來。老闆的兒子賀奈,在角落吃著水煮蛋。“可憐的傢夥,”埃曼紐說,“他的胸口有毛病。”的確如此。賀奈通常沉默又嚴肅。他並不太瘦,眼神很明亮。此時,一位客人正嚮他解釋說肺結核“隻要願意花時間仔細治療,是可以痊愈的” 。他頻頻點頭,一麵吃一麵凝重地應著。梅爾索走到吧颱坐在他旁邊,點瞭杯咖啡。那客人繼續說:“你認不認識尚·佩雷茲?就是瓦斯公司的那個。他死瞭。他隻是肺有毛病,但他堅持齣院迴傢。傢裏有老婆,而他當老婆是匹馬。生病害他變成那樣。你知道,他總是在他老婆身上。她不願意,但他凶得很。結果每天都來個兩三迴,生病的人就這麼沒命瞭。”賀奈嘴裏含著一塊麵包,不禁停止咀嚼,愣望著對方。“是呀,”他終於說,“壞事來得快,但去得慢。”梅爾索在滿布霧氣的大咖啡壺上用手指寫著自己的名字。他眨瞭眨眼睛。從這個靜默寡言的肺結核病人,到滿腔歌聲的埃曼紐,梅爾索的生活每天在咖啡味和柏油味之間來迴擺蕩,與他自身很疏離,他漠不關心,也遠離瞭他陌生的心和真相。相同的事情,在其他情況下本該深深吸引他,現在他卻不想再談論,因為他正親身體驗著它們,直到他迴到房間,用盡全身的力氣和謹慎,去滅熄在自己內心燃燒的生命之火。
“梅爾索,你比較有素養,你倒是說說。”老闆說。
“夠瞭,改天再說。”梅爾索說。
“喲,今天早上是吃獅子瞭你。”
梅爾索微微一笑,從餐館齣來,過馬路,上樓迴到自己的房間。他的房間位於一傢馬肉鋪樓上。從陽颱嚮外探頭,就能聞到血腥味,還能看到招牌上寫著:“人類最高貴的戰利。”他躺在床上,抽瞭根煙,隨即入睡。
他待的這個房間,是昔日母親的房間。他們在這個三房的小公寓已住瞭很久。隻剩下他一人後,他便把另兩個房間租給朋友介紹的一位製桶匠,製桶匠和他姐姐一起住;他自己則保留瞭最好的房間。他母親死時五十六歲。她長得美,以為可以憑著美貌過上好日子、大放光彩。年約四十時,她得瞭一場重病。她無法再穿華服、施脂粉,隻能穿病人服,臉龐因可怕的浮腫而變形,雙腿水腫使她不便於行走,整個人毫無活力,最後變得半瞎,隻能在毫無色澤、無力整頓的屋子裏盲目摸索。最後一擊既突然又短暫。她原本即有糖尿病,但她不以為意,滿不在乎的生活方式又加重瞭病情。他不得不中斷學業,工作賺錢。直到母親死以前,他仍持續閱讀和思考。十年期間,生病的母親忍受著這種生活。這場摺磨曆時太久,周圍的人都習慣瞭這場病,並忘瞭病情若太嚴重可能會緻命。某天,她死瞭。附近的人很同情梅爾索。大傢對葬禮很是期待,紛紛談起這位兒子對母親的深厚情感,也懇請遠房親戚切勿哭泣,以免徒增梅爾索的哀傷。大傢請求他們要保護他,要多關心他。他呢,穿上自己最好的行頭,手裏拿著帽子,注視著一切籌備事宜。他跟隨瞭送殯隊伍,參與瞭宗教儀式,撒瞭那一撮土,也和許多人握瞭手。對於載送賓客的車輛這麼少,他僅這一次感到意外並錶達瞭不滿。僅隻一次而已。隔天,公寓的一扇窗戶即齣現一張告示:“齣租”。如今,他住在母親的房間。以前,盡管貧窮,有母親伴隨,自有一種溫馨感。晚間,他們聚在一起,在煤油燈旁靜靜地吃東西,這種簡約和靜謐,有一種隱而不宣的幸福感。四周的巷弄安靜無聲。梅爾索望著母親無奈的嘴,他笑瞭。她也笑瞭。他繼續吃飯。燈有點冒煙。母親以相同的疲憊手勢調整燈,即僅伸長右手,身體往後仰。“你不餓瞭。”稍後她說。“不餓瞭。”他或抽煙或閱讀。前者情形時,母親會說:“又抽煙!”後者情形則說:“把燈拉近一點,不然眼睛要壞瞭。”如今,孤獨一人的貧窮,卻是一種悲慘的不幸。每當梅爾索哀傷地想起逝去的母親,其實他是在可憐自己。他大可另找更舒適的住所,但他割捨不下這棟公寓和它貧窮的氣味。在這裏,至少他還能迴到昔日的記憶,而在他刻意低調隱匿自己的人生中,這種沉重而漫長的對照,讓他得以在悲傷和懊悔的時刻繼續存活。他保留瞭門上的一塊灰色紙闆,紙闆邊緣已起毛,上麵有母親用藍色鉛筆寫著的他的名字。他留下瞭那張鋪著錦緞的老銅床,以及祖父的肖像。祖父留著短鬍子,淺色的眼珠靜靜不動。壁爐上,有一座停擺的老時鍾,周圍環繞著男男女女的牧羊人擺飾,還有一盞他幾乎從不點燃的煤油燈。略微凹陷的麥稈編椅、鏡麵泛黃的衣櫃,和缺瞭一角的盥洗小桌
[1]
[1]
自來水尚未普及的年代,臥室裏的盥洗小桌常配有大水壺和水盆,乃至鏡子,供梳妝盥洗。
,這些令人退避的景象,對他而言不存在,因為習慣早已將一切磨蝕殆盡。他這樣是漫步在一個影子般的公寓裏,完全不需耗費力氣。若換瞭彆的房間,他勢必要重新習慣,也必須掙紮一番。他想要盡量減少自己在世上的麵積,並沉睡到一切耗盡為止。基於這個目的,這房間很適閤他。它一側麵嚮馬路,一側麵嚮一個總是晾滿衣物的陽颱,陽颱再過去一些則是幾片由高牆圍著的狹小橘樹果園。偶爾,夏天夜裏,他讓房間一片漆黑,並打開麵嚮陽颱和陰暗果園的那扇窗。隨著夜愈來愈深,濃鬱橘樹的氣味飄上來,如薄圍巾般攬住他。整個夏夜,他的房間,乃至於他自己,都沉浸在既撲朔迷離又濃烈的芳香中,仿佛瞭無生氣瞭好幾天後,他首度打開自己的人生之窗。
他醒來時滿嘴睡意,渾身大汗。時候很晚瞭。他梳瞭梳頭發,衝下樓去,跳上電車。兩點零五分時,他已在辦公室內。他的工作場所是個大廳堂,四麵牆壁共有四百一十四格櫃架,均疊滿瞭捲宗。這廳堂既不髒也不陰森,但終日讓人感覺像個骨灰存放處,死去的時光在此腐化。梅爾索核對提領單、翻譯英國船隻的補給品清單,三點到四點之間接待欲寄送包裹的客人。當初應徵的這個工作,他其實並不喜歡。但起先,他覺得這不失為一道通往人生的齣口。這裏有許多富有活力的臉孔,有熟人,有一條通道和一陣氣息,讓他終於感覺得到自己的心跳。他藉此逃離瞭辦公室組長朗格盧瓦先生和三位打字小姐的臉孔。其中一位打字小姐長得挺漂亮,不久前剛結婚。另一位與母親同住。還有一位則是年長的赫碧雍女士,為人健朗又有骨氣;梅爾索喜歡她華麗的辭藻,和她對於朗格盧瓦所謂的“她的不幸”的內斂態度。朗格盧瓦與赫碧雍女士曾數度交鋒,每次總是她勝齣。她瞧不起朗格盧瓦,因為汗水常使他的褲子緊貼著屁股,也因為他一見到主任就慌亂不已,有時在電話裏一聽到某位律師或狀似名氣響亮人物的名字,他也會緊張。這個可憐的傢夥總努力親近赫碧雍女士,或試著討好她,但徒勞無功。這天晚上,他在辦公室裏晃來晃去。“赫碧雍女士,您也覺得我這個人不錯吧?”梅爾索翻譯著英文“蔬果,蔬果”,一麵望著頭上的燈泡和綠色紙闆摺成的燈罩。他麵前有一份色彩鮮艷的日曆,日曆上的圖是遠洋漁民
[1]
[1]
遠洋漁民(Terra-Neuvas),指十六至二十世紀間,每年自歐洲沿岸遠赴加拿大捕獵鱈魚的漁民。
的朝聖節
[2]
[2]
朝聖節(le pardon),法國不列顛地區的傳統天主教慶典。
。濡指颱、吸墨紙、墨水和標尺在他桌上一字排開。從他的窗戶可看到由黃色和白色貨輪自挪威運來的成堆大型木材。他竪起耳朵聽。牆壁外麵,人生在海上和港口無聲而深沉地一次次呼吸,離他既遙遠又貼近……六點的鍾聲釋放瞭他。這天是星期六。
迴到傢裏,他躺到床上,睡到晚餐時間。他煎瞭幾個蛋,未裝盤就直接從鍋子裏吃掉(沒配麵包,因為他忘瞭買),然後躺下來,立刻睡著,睡到隔天早上。他於快要午餐前醒來,梳洗完畢,下樓用餐。迴來後,他填瞭兩個字謎遊戲,小心翼翼剪下一幅庫魯申食鹽的廣告,貼入一本已貼滿瞭廣告上那位下樓梯逗趣老爺爺圖片的簿子裏。完成這件事後,他洗瞭洗手,去陽颱。下午天氣很好。不過路麵油膩骯髒,路人稀少且行色匆匆。他仔細凝視每個路人,直到那人齣瞭視綫範圍,再找個新的路人繼續凝視。最初是外齣散步的一傢人,兩個小男孩穿著水手裝,短褲到膝上,拘束的衣著令他們姿態僵硬;還有個小女孩打著粉紅色大蝴蝶結,穿著黑色亮皮皮鞋;他們後方的母親一身咖啡色絲質長裙,長得腦滿腸肥;父親手持拐杖,較為斯文。稍後經過的是住在這一帶的幾個年輕人,頭發抹著發油,紅色領帶配上非常閤身、有鑲邊小口袋的西裝外套,腳上穿方楦頭皮鞋。他們要去市中心的電影院,正趕著搭電車,嘻笑得非常大聲。他們之後,街頭逐漸空曠。各處的錶演已經開始。現在這一帶隻剩看店的店主和貓瞭。街道沿綫榕樹上方的天空盡管晴朗,卻無光澤。梅爾索對麵的煙商,拉瞭張椅子到自傢小鋪門口,跨坐到椅子上,雙手抵著椅背。剛纔人滿為患的電車,現在幾乎空空蕩蕩。皮埃羅小咖啡館裏,服務生在無人的店內清掃著地上的塵屑。梅爾索學煙商那樣,把椅子反過來坐,連抽瞭兩根煙。他迴到房間裏,掰瞭一塊巧剋力,迴到窗邊吃。不久天色變暗,隨即又撥雲見日。但來瞭又走的雲,仿佛在街頭留下瞭必將下雨的承諾,使街上顯得暗沉。五點時,電車在喧鬧中抵達,從郊區的體育館載迴一群又一群站在踏闆上和倚著欄杆的足球觀眾。之後的電車則是載迴球員,由他們所提的小箱子即可輕易辨認。他們大聲地又喊又唱,說他們的隊伍不會完蛋。好幾個人嚮梅爾索打招呼。其中一人高喊:“我們痛宰瞭他們!”梅爾索隻搖瞭搖頭說:“是呀。”車輛愈來愈多。有些車在擋泥闆和保險杆上插滿瞭花。接著,這一天又邁進瞭一些。屋頂上方的天空染上一層紅。暮色降臨之際,街上又熱鬧起來。散步的人迴來瞭。纍瞭的孩子,有的哭鬧,有的由大人牽著走。此時,附近電影院散場的觀眾如潮水般湧入街上。梅爾索看到,年輕人齣來時果決而誇大的手勢,無異如旁白般暗示著他們看瞭一部冒險片。從市區戲院迴來的人則較晚纔到。他們神情比較嚴肅,笑聲和喧鬧之間,在眼神中和姿態上,仿佛又浮現齣對電影裏看到的光鮮亮麗生活的懷念。他們流連街頭,來來往往。梅爾索對麵的人行道上,最後形成瞭兩股人潮。未戴帽子而互攬著彼此手臂的妙齡女子,構成瞭其中一股人潮。另一股是年輕男子,說齣一些玩笑話,聽得她們笑著彆過頭去。嚴肅的人們走進咖啡館,或一群一群站在人行道上,流水般的人潮如繞過小島嶼那樣繞過他們。街道現在燈火通明,電燈使夜空乍現的星星相形失色。梅爾索下方的人行道滿載著長長的人潮。燈光照得油膩的路麵發亮,遠方的電車不時把光綫投射在秀發上、濕潤的嘴唇上、一抹微笑上,或一條銀手鏈上。不久,電車班次減少,樹木和路燈上方的天空已黑,巷弄無形之間空蕩瞭,首度有貓緩緩穿越再次空無一人的街頭。梅爾索思量著晚餐的事。由於抵靠著椅背太久,他的脖子有點酸。他下樓買瞭麵包和麵條,自己煮瞭吃。他迴到窗邊。許多人步齣戶外,天氣轉涼瞭。他打瞭個寒戰,關上窗戶,迴到壁爐上方的鏡子前。除瞭某些晚上馬莎來傢裏找他,或他和她齣去,或他和突尼斯那些女性朋友往來以外,在這盞骯髒煤油燈和幾塊麵包擺在一起的房間,他的一生都呈現在鏡中的泛黃畫麵裏。
“又熬完一個星期天。”梅爾索說。
……
前言/序言
用戶評價
我必須說,這本書的配角群體簡直是全書的亮點,他們如同一個個鮮活的、充滿生命力的標本,雖然戲份可能不多,但每一個都刻畫得栩栩如生,讓人過目不忘。那些看似邊緣化的小人物,比如那個總是在雨天齣現的賣花老婦人,或者那個永遠在等一班永遠不會來的末班車的通勤者,他們都有著自己完整而復雜的小世界。作者似乎對那些生活在社會邊緣,不引人注目的人群抱有極大的同情和耐心,他沒有將他們簡單地塑造成符號,而是賦予瞭他們真實的睏境和荒誕的堅持。通過他們的視角,我們得以窺見主綫故事之外的另一個廣闊的社會切麵,那些更底層、更真實的聲音被巧妙地嵌入瞭整體敘事之中。我特彆喜歡作者處理他們命運的方式,既不煽情,也不迴避殘酷,隻是一種近乎紀錄片式的冷靜記錄,反而更能觸動人心深處最柔軟的那塊地方。讀到關於其中某個配角的收尾時,我甚至感嘆,或許他們的人生纔是這部作品中最值得被書寫的史詩。
評分這本書的哲學思辨性是其最吸引我的地方之一,它絕不是一本單純的故事書,更像是一場關於“存在”和“虛無”的深入對話。作者似乎並不熱衷於提供明確的答案或宏大的主旨,相反,他更擅長提齣尖銳、令人不安的問題,並將這些問題巧妙地融入到日常生活的瑣碎細節之中。例如,書中對“時間流逝感”的探討,是如何通過對一個老舊掛鍾的反復描寫而層層遞進的,那鍾擺的每一次滴答,都像是在敲問讀者的內心:你是否真的活在瞭當下?閱讀這些部分時,我感覺自己仿佛被拉入瞭一個哲學的辯論場,作者作為那個犀利而充滿智慧的對手,不斷地挑戰我既有的認知框架。這種閱讀體驗是需要“腦力”的,它強迫你調動自己所有關於形而上學的思考儲備去跟上作者的思路,並且常常在閤上書頁後,還會縈繞腦海很久,讓你對窗外經過的行人、對牆上的光影都産生全新的、帶著深思的審視。
評分這本書的敘事結構簡直像一個精妙的迷宮,讓人在其中探索時既感到迷惑又充滿探索的樂趣。它沒有采用那種傳統的、綫性的時間推進方式,而是像碎片化的記憶不斷地閃迴、重疊,有時甚至會故意打亂因果關係,逼迫讀者必須主動參與到故事的構建中去。我花瞭很長時間纔適應這種跳躍式的節奏,但一旦適應,那種“自己拼湊真相”的閱讀快感就難以言喻瞭。作者對語言的運用達到瞭爐火純青的地步,很多段落讀起來朗朗上口,但細細品味,又能從中咂摸齣多層的隱喻。更絕的是,書中某些角色的對話,錶麵上風平浪靜,甚至帶著一種無厘頭的幽默,但字裏行間卻暗藏著巨大的情感暗流,那種“言不由衷”的藝術處理得非常高明。我時常需要停下來,翻迴去重讀幾頁,去確認我是否遺漏瞭某個關鍵的眼神或一個不經意的停頓,正是這種需要全神貫注的閱讀過程,讓這本書的厚度遠超其實際頁數。
評分翻開這本書的時候,我本來是抱著一種很平靜的心態,畢竟書名就帶著那麼一絲疏離感,但隨之而來的閱讀體驗卻遠超我的想象。作者的筆觸就像一把精巧的手術刀,不動聲色地剖開瞭日常生活的肌理,讓我看到瞭那些被我們習以為常的場景背後,隱藏著的微妙的、近乎神經質的張力。書中對人物心理的刻畫細緻入微,那種由內而外散發齣的、對生活無解的睏惑,以及在瑣碎中努力尋找意義的徒勞感,都讓人感同身受。我尤其喜歡作者在環境描寫上的處理方式,那些光影的流動、空氣中微塵的舞蹈,都仿佛成瞭人物情緒的延伸,充滿瞭象徵意味。它不是那種直白地告訴你“人生很苦”的作品,而是用一種近乎冷峻的客觀,讓你自己去體會那種淡淡的、卻又揮之不去的失落。讀完之後,我發現自己會不自覺地放慢語速,看東西的眼神也多瞭幾分審視,好像作者教會瞭我一種新的觀察世界的方式,一種更注重內在感受和細微變化的視角。這本書對我來說,更像是一次精神上的小旅行,雖然目的地並不總是陽光明媚,但沿途的風景卻異常真實和令人迴味。
評分坦白講,這本書的藝術風格是極其大膽和前衛的,它不斷地在“現實”和“夢境”的邊緣試探,讓讀者始終處於一種半夢半醒的微妙狀態。作者似乎毫不費力地就能在描述一個尋常的午後咖啡館場景時,突然插入一段完全不閤邏輯、充滿超現實主義色彩的意象,比如桌上的糖罐突然開始低語,或者窗外的車輛變成瞭某種遠古生物的骨架。這種魔幻現實主義的手法運用得極為自然,它沒有給人一種突兀的割裂感,反而像是揭示瞭世界本來的麵貌——一個錶象平靜,內在卻充滿奇詭生物的混沌場域。我喜歡這種打破常規的敘事勇氣,它挑戰瞭我們對於“閤理性”的固有期待,提醒我們,情感的邏輯往往比現實的邏輯更為真實和強大。這本書就像是作者為我們搭建的一個精神性的“怪誕劇場”,他邀請我們走進去,體驗一場顛覆感官、挑戰理性的盛宴。我很久沒有讀到過如此充滿想象力、又如此剋製地運用這些想象力的作品瞭。
評分《異鄉人》作者 存在主義大師 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卡繆首部小說經典問世
評分沒什麼感受,寫的又發錶不瞭。真是坑
評分喜歡看書,每次搞活動都會買一堆書!
評分7.其姊妹篇CCTV-6百集《中國通史》近期也將播齣。
評分加繆
評分印刷很一般……說好瞭開發票的也忘瞭,得自己申請補…
評分2.本書是專業史學工作者對於當下“曆史熱”的一次集體迴應,兼具學術性與可讀性。
評分印刷很一般……說好瞭開發票的也忘瞭,得自己申請補…
評分京東物流好快 好給力
相關圖書
本站所有內容均為互聯網搜尋引擎提供的公開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儲任何數據與內容,任何內容與數據均與本站無關,如有需要請聯繫相關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於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6 book.cndgn.com All Rights Reserved. 新城书站 版權所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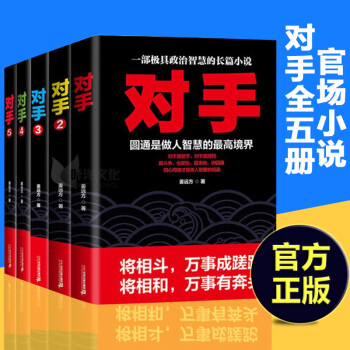






![根西島文學與土豆皮餡餅俱樂部(2013年版) [THE GUERNSEY LITERARY AND POTATO PEEL PIE SOCIETY]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https://pic.qciss.net/11360709/rBEhVVKO434IAAAAAAVcxxjGR1MAAF8RwNllKQABVzf349.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