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过欲望之城 [How to Get Filthy Rich in Rising Asia]](https://pic.qciss.net/12283390/5a55ccc7N3154adae.jpg)

具体描述
产品特色
编辑推荐
◆《穿过欲望之城》被美国国家公共电台评为“国际版的《了不起的盖茨比》”!
◆《穿过欲望之城》接连被15家世界主流媒体评为年度图书!
◆《穿过欲望之城》让各国读者争相推荐这部令人笑中带泪的小说!
◆《穿过欲望之城》是文坛鬼才莫欣·哈米德的重要代表作!
◆我奔走一生追求金钱,最后才发现我真正渴望的是爱。
内容简介
在一个偏僻的村庄里,有一个从没见过滑板车、巧克力或是运动鞋的男孩。一天,他的父母决定举家搬到城市里居住,男孩的命运也随之迎来巨大的转折。
就如同所有大城市一样,男孩的新家是一个蕴含着无限可能的地方。他暗暗下定决心,自己人生的目标就是成为有钱人。为了这个目标,他可以付出一切代价。
男孩把握住了每一个机会,命运也眷顾了他。然而随着年龄的增长,他渐渐意识到了自己真正渴望什么……
作者简介
莫欣·哈米德:
莫欣·哈米德,文坛鬼才,曾多次入围布克奖。他的代表作累计销量过百万,并被《卫报》选入“定义了十年来的世界”书单。
1993年,莫欣·哈米德以头等荣誉学位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随后于1997年毕业于哈佛法学院。大学期间,莫欣·哈米德曾向著名作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托妮·莫里森学习写作。
《穿过欲望之城》是莫欣·哈米德的代表作之一,一经出版就受到了西方各大媒体的赞誉。美国国家公共电台称它是“国际版的《了不起的盖茨比》”。《纽约时报》也因为《穿过欲望之城》称赞莫欣·哈米德是“这个世代举足轻重的小说家”。
精彩书评
令人眩晕。令人上瘾。莫欣·哈米德运用他高超的写作能力,讲述了一个美妙的故事。一本无与伦比的小说:柔软、尖锐又大胆。——《卫报》
全书只有十二个章节,干脆利落,却是一场了不起的旅程。——《经济学人》
《穿过欲望之城》的感情如此丰富,对生命意义的讨论也直击要害。——《华盛顿独立书评》
莫欣·哈米德无疑满足了读者的期待。《穿过欲望之城》不可思议又感人至深。——《时代周刊》
简直无与伦比。——《每日邮报》
这部小说体现出了作者的野心。精妙又丰富。 ——《出版人周刊》
目录
1 搬到大城市
2 接受教育
3 不要堕入爱河
4 远离理想主义者
5 向大师学习
6 为你自己工作
7 做好使用暴力的准备
8 和当官的做朋友
9 保护战争艺术家
10 与债共舞
11 聚焦根本
12 准备好退出策略
精彩书摘
你所在的班级有50个学生,但桌椅只够30个人用。其他人都坐在地板上或站着。教你的是个面颊凹陷、成天满地吐槟榔、看上去很可能有结核病的男老师。今天他教你背乘法表。他喜欢,或者说只会用一种漫不经心的吟唱来教授这种需要死记硬背的教学工具。他思维里不负责控制发声器官的那一部分仿佛已经脱离了他的身体,越走越远。
你的老师唱道:“十十一百。”
全班同学一起重复了一遍。
你的老师唱道:“十一十一一百二十一。”
全班同学又一起重复了一遍。
老师再唱:“十二十二一百三十四。”
一个莽撞的声音纠正道:“一百四十四。”
教室突然陷入了沉寂。那是你的声音。你在张嘴前并没有思考,至少没有充分地思考。
你的老师问:“你说什么?”
你犹豫了。但一切已经发生了。无法回头了。
“四十四。”
老师的声音温柔却带着威胁:“你为什么这么说?”
“十二乘以十二等于一百四十四。”
“你觉得我是傻瓜吗?”
“不是的,先生。我以为您说的是一百三十四。我听错了。您说的是一百四十四。对不起,先生。”
全班同学都知道老师并没有说一百四十四。或者不是全班。大部分人根本就没有听讲,想的都是放风筝、冲锋枪或用拇指和食指把鼻涕揉成一个球。但有些人确实听到了。所有人都知道将会发生什么,虽然他们不知道具体的形式。他们充满恐惧地观望着,一如礁石上的海豹,观察着不远处跃出水面的大白鲨。
你们中的大部分人都被老师惩罚过。作为全班最聪明的学生,你受到过几次最严厉的惩罚。你想要隐藏自己的知识,但冒险精神却经常压倒你的理智,每每如此,你都要付出代价。今天,你的老师把手伸进了短上衣的口袋里,那里面放了一些粗沙。然后他揪住了你的耳朵,手上的粗沙加大了摩擦,你的耳垂顿时血迹斑斑。你忍着不哭出声来,不让施酷刑的人感到满足,但这无非是让灾难变得更为长久。
你的老师并不希望当老师。他本来想当电表工。查电表不用和孩子打交道,工时较短,更重要的是可以收取些贿赂,既能赚钱,社会地位又高。他倒不是没有能力查电表。他的叔叔就在电力部门工作。但这份查电表的工作和他人生中其他向往的事情一样,在他叔叔的帮助下,最终落到了他哥哥的头上。
后来,你的老师虽然在初中结业考试中落败,却想办法修改了成绩,再用相当于他之后工资60%的钱贿赂了在教育部门当小科员的表亲,以获得现在的教职。他绝非一个以教育为人生目标的人。恰恰相反,他憎恨教书。这让他感到羞耻。尽管如此,他还是会担心失去这份工作,担心自己的体罚行为被发现,然后要付出更大的代价去保留这份工作。他的担心由于长期的失望和对世界不公的坚定看法而日益加深,并暴露在他成瘾般的暴力行为中。每次动手时,他都告诉自己,他是在把教育灌输进又一个愚蠢的头脑。
灌输和教育,这两者相互交织,纠缠在你周围很多人的生活里。比如你的姐姐。你回家的时候她正在哭。最近她的情绪一直在被压抑的大颗泪珠和冷漠的倨傲态度之间徘徊。此刻是前者。
你说:“又怎么了?”
“别惹我,混球。”
你摇了摇头。此刻的你太过虚弱,没法做出合适的回应,也没力气去挨她的耳光。
她发现你有点儿不对劲。她问:“你的耳朵怎么了?”
“老师。”
“那个狗娘养的。过来。”
你坐在她旁边。她用手环着你,抚摸着你的头发。你闭上了双眼。她吸了几次鼻子,但已经不哭了。
你问:“你害怕吗?”
“害怕?”她强笑了一下,“他应该怕我。”
“他”指的是你父亲的二表弟,比她大十岁,现在和她订了婚。他的第一个老婆在分娩的时候死了,之后他马上就找上了她。
“他还留着胡子吗?”你问。
“我怎么知道?我好多年都没见过他了。”
“那胡子真厚。”
“你知道他们怎么说男人的胡子吗?”
“怎么说?”
“算了。”
“你害怕吗?”
“怕什么?”
“我不知道。害怕离开这儿。我就害怕一个人回村。”
“所以你还是男孩儿,而我是女人。”
“你是女孩儿。”
“不,我是女人。”
“女孩儿。”
“我每个月都流血。我是女人。”
“你真恶心。”
“可能吧。”她笑了,“但我是女人。”
然后她做了一件让你惊讶的事。她做了一件在你心中只有身材婀娜的女人——而不是像你姐姐一样瘦削单薄的女孩儿——才会做的事。她居然唱起歌来。她的声音轻柔,却极具力量。她唱了一首你的村子里的母亲们给新生儿唱的歌。这首歌你的母亲为你们每个人都唱过:像是摇篮曲,但曲调更活泼一些,不是为了让婴儿入睡,而是希望母亲不在眼前时,婴儿也能感到她的存在。你已经很多年没有听到过这首歌了。听到你姐姐唱它,你感到有些奇怪,放松的同时又感到不安。你靠着她,感到她的身体一张一弛,仿佛一台风琴。
她唱完后,你说:“咱们去河边吧。”
“好。”
你们两个人离开了一家人合住的那个房间。这里和你在村子里的家差不多,只不过外墙是砖头砌的,而不是泥土垒成的,位于一栋摇摇欲坠的三层小楼的顶层。你顺着楼梯扶手滑到了一层,走进了一条从主道岔出来的偏僻的窄巷。这巷子是条死胡同,哪里也通不到,三面都是住家。巷子里垃圾成山,后面是一条露天的阴沟。
如果有人从侦察卫星上观看,会发觉两个孩子的行为十分古怪。他会看到他们非常小心地走向那条阴沟,仿佛里面不是各种黏稠的污物,而是湍急的洪流。而且虽然这条阴沟很浅,轻轻一跳就可以越过去,两个孩子还是小心地站在沟的两边,两只手圈在嘴边,仿佛彼此间的距离远到需要大喊才能让对方听到。达成协议之后,其中一个孩子捡起了一根铁丝——看上去应该是人家扔掉的自行车车条——好像在用它钓鱼,虽然没有鱼线和鱼钩,这里显然也不可能钓到任何东西。另一个孩子则拿着一长条棕色的包装硬纸板往沟里戳:在戳透明的海龟吗?还是隐形的鳄鱼?实在很难理解她莫名其妙的行为。突然,那个女孩儿蹲下身,看上去好像在生火。男孩冲她喊了句什么,她便把围巾的一端抛给了他。
你紧紧地揪住她的围巾。在你手中,它变成了帮你过河的绳索。但就在你过河之前,咒语被打破了。你顺着你姐姐的目光望去,那扇刚刚还关着的窗户打开了。一个高个子的秃头男人站在屋里,目光炽热地看着你姐姐。她拿走了你手中的围巾,一端围住头,另一端遮住她小小的胸脯。
“我们回家吧。”她说。
你姐姐在你家搬来城市之后没多久就开始帮人打扫房间赚钱了。你父亲微薄的收入很难追赶近年来疯狂的通货膨胀。你父母告诉她,你哥哥工作之后她就可以回学校读书了。她只上过几个月的学,但对学习的热情比你上学多年的哥哥要高得多。
你哥哥现在已经成为了一个油漆工的助理,也就不再读书了。但你姐姐并没能回到校园。她已经错过了时间。婚姻才是她的未来。她已经被打上了进入婚姻的标记。
你们到家的时候,你哥哥正坐在房间里。他看上去精疲力尽,满手满脸都是白色的油漆,就连头发里都是,就像一个化装成中年大叔的小男孩要在学校演出。他疲惫地看着你们,咳了几声。
你姐姐说:“我告诉过你别抽烟。”
他说:“我没有抽烟。”
她哼了一声:“你抽。”
“是我老板抽的。我一整天都跟他在一起。”
事实上你哥哥有时候确实会抽烟,但他自己并不喜欢,而这一个星期他都没碰过香烟。况且烟草并不是造成他咳嗽的原因。真正的源头是涂料。
每天早晨你哥哥都要穿过铁路。人行道没封闭的时候他可以直接穿过去,如果封闭了,但火车开得很慢,他会像玩游戏一样淘气地跑过去,然后搭公车到算不上古老也算不上年轻的欧洲风格百年老区去上班。他穿过一间茶叶铺,走进一片露天区域,这里曾经是一个公共广场,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一个公共的梯形空间。但如今,因为一些非法建筑堵住了它的一条通道,这里变成了一个完全封闭的露天小院。
院子在多功能规划,或者更应该叫没有规划,可谓登峰造极。周边建筑的楼上有一些民宅和工人住的出租房,一个破酒店的客房,以及裁缝店、刺绣工和其他工匠的工坊,还有两个私家侦探的办公室,这两个人互相憎恨,经常通过窗户相互观察。在一层,楼的正面——也就是不朝着小院的那边——是商店和几间简陋的饭店;而朝着院子的那面则租给了一间小规模的工厂:对这个高人口密度的区域来说,它从听觉、嗅觉、视觉上都很不受欢迎,因此只能把朝着封闭院落的这一边作为遮挡自己的面纱。
你哥哥帮忙的这个油漆工是做空气喷涂的。他们今天的活计来自一个声名显赫的室内装修设计师。你哥哥从一辆小卡车上卸下了一套定制嵌入式书架。书架还没涂油漆,也就不能嵌到墙里去。他小心翼翼地抬着书架穿过茶叶铺进入小院,走进了油漆工的棚子,脚步因为负重有些蹒跚。他把塑料布贴在房顶上作帘子,防止油漆溅到已经漆好、等着客户来取的家具上,然后用报纸包住书架上的氖光灯和金属电灯开关,再按照油漆工的指示把颜料和底漆混好,拉好插线板,插好喷枪。然后他便站在油漆工身后,在闷热的房间里大汗淋漓地看着油漆工拿着喷枪一行行地为书架喷漆,如同汽车装配厂的机器人,但比机器人少了些精确,多了些汗水。每过几分钟,你哥哥都会跑去清理溅出来的油漆,或者搬梯子,打水,买面包,重新接电线。
你哥哥的工作从某种意义上讲接近宇航员,或者换个沉闷些的比喻,更像是带水肺的潜水员:都包含了空气的嘶嘶声、失重的感觉、突然的头痛和恶心,以及有机体和机器融合在一起时的那种不稳定感。然而,宇航员和潜水员都可以看到一个崭新的世界,但你哥哥每天看到的仅仅是不同浓度的单色糨糊而已。
他的职业要求他具有耐心和承受不断的低度恐慌的韧劲,这两者你哥哥都不具备。此外,在理论上,它还需要护目镜和防毒面具,但无论是你哥哥还是他老板都没有这些,他们只是用一些薄棉布蒙住嘴巴和鼻子。这样做的短期结果是咳嗽,而长期结果可能会非常严重。但给油漆工当助手是有工资的,能学到宝贵的技术,而且每个人都知道,从长远来看,没有什么事是完全不可能造成人的死亡的。
那天晚上你母亲做的是炖豆角,里面放了很多洋葱。这并不是因为你母亲非常喜欢洋葱,而是因为它们可以让菜显得更丰富,而且今天洋葱又比较便宜。你并不是一个好运的孩子。你耳朵上的伤看上去比你姐姐的目光或你哥哥皮肤上的油漆要更痛苦一些。但你还是幸运的。因为你是家里第三个孩子。
在迅速崛起的亚洲,受教育可以让你向富有跨出一大步。这不是什么秘密。但和很多令人向往的事情一样,大家都知道,并不意味着大家都能做到。有些人一生都走在通往财富的路上,无需选择、欲望或努力,有些人只需要机会,而你,借助的却是你在家里孩子中的排位。作为第三个孩子,你不需要回到村子里,不需要成为油漆工的助手,不需要像你家第四个孩子一样躺在村子里大树下面的坟墓里。
你的父亲在晚饭后回到了家。他一般都是在他干活的那家和其他用人一起吃饭。你们全家都围在电视机周围,这是你们的城市繁荣的一个象征。电是从你家前面那座大楼偷来的。那是一台陈旧的阴极射线管黑白电视机,屏幕凹凸不平,上面还有恼人的裂纹。它的大小还不及你手腕到手肘之间的长度,只能收到几个全球播出的频道。但它至少可以看,而你们全家都鸦雀无声,无限欣喜地看着它带到你们房间的这场音乐演出。
演出结束后,字幕出来了。在你母亲看来,那只是一些毫无意义的象形符号,你父亲和姐姐认识其中的一些数字,而你哥哥则懂得其中的一些单词。只有你知道这些文字的意义。你明白这是表演者名单。
就在这个时候,你居住的这个区域整个停电了,你家那个光秃秃的灯泡也同时灭掉了。你们点了蜡烛,准备就寝。最后你母亲用手指把烛芯掐灭了。
房间里昏暗但并不漆黑。城市的夜光从百叶窗缝间钻了进来。一切归于安静,但并非鸦雀无声。你听到火车减慢了速度。虽然你们挤在一张小床上,你还是沉入了梦乡。你哥哥的咳嗽居然一次都没能把你吵醒。
前言/序言
用户评价
这本小说的叙事节奏着实让人着迷,作者对于人性的洞察力简直达到了令人惊叹的程度。读下去的时候,我感觉自己就像是掉进了一个精心设计的迷宫,每转一个弯,都能发现一些关于欲望、野心与妥协的全新维度。那种细腻的心理刻画,不是那种直白的宣泄,而是像一层薄雾一样,慢慢地、不着痕迹地渗透进读者的意识深处。我特别欣赏作者对于环境描写的笔触,它不是简单的背景板,而是故事中一股强大的驱动力,它塑造了人物的命运,也反过来被人物的挣扎所扭曲和映照。你会清晰地感受到那种向上攀爬的焦灼感,那种被时代洪流裹挟着身不由己的无奈,却又时不时闪现出个体在绝境中爆发出的惊人韧性。这本书的魅力就在于,它没有给出简单的答案,而是将所有复杂的情感和矛盾摆在你面前,让你自己去品味那种甜腻中带着苦涩的滋味。那种对“成功”的定义,在故事推进的过程中,不断地被挑战和重塑,直到最后,你可能对自己最初的理解都产生了动摇。
评分读完合上书本的那一刻,我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后遗症”——对周围世界的观察角度似乎被永久性地改变了。这本书成功地构建了一个自洽的微观宇宙,在这个宇宙里,规则比法律更有效,而“欲望”才是唯一的通行证。它巧妙地将宏大的社会议题,通过一系列极具代入感的个体奋斗故事来呈现,使得那些抽象的概念变得可触摸、可感知。我尤其佩服作者在塑造核心人物群体时的平衡感,他们既是受害者,也是施害者,这种双重身份的构建,使得人物形象丰满立体,拒绝扁平化。读者很难完全站在某一边去评判,更多的是陷入一种理解与挣扎的复杂情感中。这本书的力量在于,它不是在教导你该做什么,而是在让你清晰地看见,在特定的环境下,人为了达成目标,究竟能做到何种程度的自我扭曲和超越。它是一面镜子,映照出我们这个时代最真实、最赤裸的生存图景。
评分我必须承认,这本书对我既是一种震撼,也是一种折磨。震撼在于它描绘的那个世界的真实感,那种为了生存和向上爬所付出的巨大代价,让人感同身受。折磨则是因为,它毫不留情地撕开了那些光鲜亮丽的表象,露出了下面腐朽和不堪的一面。它没有给你一个传统的“好人”或“坏人”的标签,所有角色都在各自的道德灰色地带挣扎求生,他们的行为逻辑清晰可循,却又令人不寒而栗。我最喜欢书中对于“选择”后果的呈现方式,它不是简单的善恶报应,而是一种复杂的、多米诺骨牌式的连锁反应,一个微小的决定可能在多年后引发无法挽回的巨变。这种对因果链条的精妙布局,让故事充满了宿命感,但又不失个体努力的意义。它让人看完之后,会不自觉地审视自己生活中那些看似微不足道的决定,思考它们未来可能带来的深远影响。
评分这本书的文风真是让人耳目一新,它仿佛自带一种光影效果,将故事中的场景描绘得栩栩如生,但又带着一种疏离的、略显冷峻的镜头感。我仿佛不是在阅读文字,而是在观看一部节奏紧凑、运镜极其考究的艺术电影。特别是对那些快速变迁的都市景观和快速流动的财富景象的捕捉,那种速度感和冲击力是罕见的。它没有那种传统叙事中常见的絮絮叨叨,而是用极其凝练的语言,精准地击中核心情感。每一次情绪的爆发点,都处理得干净利落,没有丝毫的拖泥带水,反而因为这种克制而显得力量倍增。这种叙事方式,特别适合当下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节奏,让人在高速阅读的同时,又不会错过任何一个关键的象征意义。作者的文字功底毋庸置疑,但更难得的是他驾驭这种现代感和历史厚重感交织的叙事氛围的能力,让人在沉浸于快节奏的戏剧冲突时,仍能感受到字里行间流淌着的对世事变迁的喟叹。
评分如果说有什么词可以概括我的阅读体验,那一定是“层层剥茧”。作者在构建故事结构时,展现出了一种近乎建筑师般的精密规划。每一个看似偶然的事件,其实都埋藏着深远的伏笔,等到水到渠成之时,那些散落的线索便如同星辰归位般精准地汇聚在一起,带来一种极大的阅读满足感。我特别注意到,作者在处理不同阶层人物的对话时,那种语言的质感和语气的微妙差异处理得非常到位,简直可以称得上是一堂生动的社会学田野调查报告。那些市侩的、充满算计的,抑或是故作清高的腔调,都让人信服不已。更重要的是,它探讨了权力运作的底层逻辑,那种看不见摸不着的规则是如何支配着人们的每一个选择。读完之后,我需要停下来,做一段时间的沉思,因为这本书带来的冲击力,不仅仅停留在情节的跌宕起伏上,更多的是对于现实世界运行机制的一种更深刻的理解和反思。它迫使你直面人与人之间那种赤裸裸的利益交换关系,却又奇妙地保留了一丝对人性中美好可能性的微弱期待。
评分《穿过欲望之城》从质朴到繁华的改变,灯火阑珊深处的感悟,一个人的改变乡落与大都会的遗失纯真。每一人都有一座欲望之城,物质在我们的星球不断澎涨,失去朋友、失去至亲、失去岁月的眷恋回忆……从头到尾悲伤与讽嘲迷失的自己,回顾穿过欲望之城变化一处平静之城,全是心境之路过去现在未来。
评分最爱京东快递 公司买书 很方便
评分正品,不错,以后会常光顾的
评分此用户未填写评价内容
评分经常在京东买书 多多少少已经买了几千块钱 京东的服务确实没的说 又是很满意的一次购物
评分购买的经历比较愉快,包装都是非常好,也很干净。很期待好好愉快地买书。京东好好加油!
评分非常不错,包装很好,快递速度很快
评分这本书昨天晚上就熬夜看完了,很好看,很深刻的人生体验
评分搞活动性价比高,京东物流给力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内容均为互联网搜索引擎提供的公开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储任何数据与内容,任何内容与数据均与本站无关,如有需要请联系相关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于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6 book.cndgn.com All Rights Reserved. 新城书站 版权所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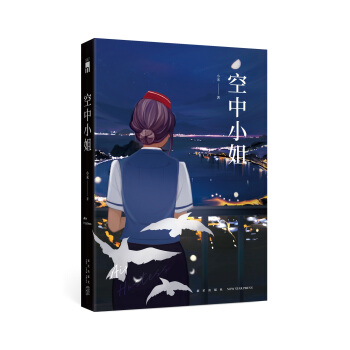

![青色时代/三岛由纪夫作品系列 [青の時代]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qciss.net/12283718/5a66a7f1Nfd3eb9fa.jpg)











![不吃鸡蛋的人 [No eggs for him]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qciss.net/12284730/5a30eab3N4b4bbb87.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