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具体描述
编辑推荐
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归根结底是农民社会的改造过程。这一过程不仅是要变农业人口为城市人口,更重要的是改造农民文化、农民心态与农民大路。内容简介
当两只小鸡在争夺一条蚯蚓时,我们能否说鸡群中存在着“私有制”?当尚未学会说话的婴儿因被人夺走奶瓶而哭闹或因“想要”而伸手去抢别人手中的玩具时,我们能否说他一出娘胎便具有了“私有者意识”?当然不能。其所以不能,是因为作为自然属性的私欲与作为一种社会规范的私有权——私有者权利观念是两种本质上不同的东西。历来我国的土地就不是(或主要不是)“按资分配”,而是“按权分配”的,最有资格当地主的并不是商人,而是权贵。有权势的江南缙绅兼并土地,无权势的关中“陕商”不置田产,都不过是这一“传统”的不同表现模式而已。
如今等级遍布、权力万能不仅已造成严重的社会病,而且使我们所讲的“阶级”概念也走火入魔,从马克思所讲的建立在“物的联系”基础上的利益集团变成了最彻底的等级——我们的“阶级成分”一度成了不因生产关系改变而改变、不因经济地位的变迁而变迁,不但决定本人命运,还可传之子孙的某种世袭身份,直到演变为“红五类”“黑五类”那样赤裸裸的现代种姓制与贱民制!
理性的觉醒决不仅仅是一个思想进化过程,它与社会化商品经济的发展、人的自由个性的发展是密不可分的。我们过去脱离后者而企图仅仅依靠宣传唯物主义与无神论来克服蒙昧与迷信,结果却在一场“无神论者的造神运动”中受到了历史的嘲弄,教训至深!
内页插图
目录
序言:“前近代”研究的当代意义绪论:农民、农民学与农民社会的现代化
第一章 欲识庐山真面目——什么是封建社会
一、“农民(peasant)”与封建社会
二、“似乎不成问题”的问题
三、从一场争论谈起
四、马克思的封建社会观怎样变成农民的封建社会观?
第二章 羌笛声中杨柳怨——旧关中小农社会分析
一、封建社会的“关中模式”
二、关于“关中无地主”
三、关中无租佃
四、关中有封建
第三章 问渠哪得浑如许、——“关中模式”的社会历史渊源与宗法农民研究中的理性重构
一、民国中前期的关中模式
二、清初以来的关中模式
三、长畛、土地流通及其他
四、“自然经济的经营地主”与“过密化”问题
五、关中模式的若干背景
六、关中模式的经验意义与逻辑意义
第四章 束缚与保护的协奏曲——封建关系的三要素
一、自然经济与“命令经济”
二、宗法共同体的“公”与“私”
三、人身依附关系:强制的与“自愿”的不自由
四、束缚与“保护”:一张恢恢天网
第五章 “朱门”之外有平均,“冻死骨”中无分化——宗法时代的社会分层
一、等级分化与阶级分化
二、宗法小农的分化与“恰亚诺夫循环”
三、宗法式社会的分化模式及其定量分析
第六章 “自由封建主义”质疑——中国封建社会特点问题
一、“亚细亚生产方式”、“商业资本主义”与“自由封建主义”
二、家-国一体的宗法共同体与“私有财产”
三、“伪商品经济”与租佃制
四、封建共同体的三种形式——我国封建人身依附关系比西方中世纪“松弛”吗?
五、“抑兼并”——仅仅是一种“欺骗”吗?
第七章 农民的塞文与农民的万代——农民在封建社会中的位置
一、农民的“两重性”质疑
二、挣脱束缚的私有者一一农民的革命性
三、渴求“保护”的共同体成员——农民的保守性
四、宗法农民的“阶层”——亚等级分析
五、既是动力,又是对象——农民与民主革命
第八章 “难对付的阶级”及其心态——宗法农民文化的社会整合
一、“东方型嫉妒”及其他——种族文化观与社会文化观
二、阿Q的劣根性是赵太爷教育出来的吗?——宗法共同体文化整合中的农民文化
三、“都市里的村庄”——为什么城里人比农民有更多的“农民意识”?
四、农民文化与“有文化的农民”——从中国知识分子传统心态谈起
第九章 “天有万物与人。人无一物与天”——“具体农民”与“抽象农民”的二重价值系统
一、宗法农民社会价值取向的二重性
二、“天有万物与人,人无一物与天”——关于“农民领袖反农民”问题
三、“农民民主主义”与近代民主制度的不同价值论基础
第十章 人性的萎缩与人情的膨胀——农民文化的伦理观探析
一、人性与人情
二、“贫农的性自由”与礼教的性禁锢
三、“人情同心圆”与农民社会的信息传播模式
四、“家族凝聚力”之谜
五、“人情同心圆”的消解与亲缘组织的“现代化”
第十一章 非理性种种——农民思维方式探析
一、中国文化是一种“理性文化”吗?
二、“理性的小农”与农民的非理性
三、宗法农民非理性的各种类型
第十二章 农民的过去、现在与未来——古典小农与古典文明
二、“五月花精神”与“美国式道路”
三、广义民主革命与农民国家的社会主义改造
四、严重的教训
五、世界“后现代化”时代的农民改造问题与社会主义民主革命的两种前途
结束语 从田园诗到狂想曲
精彩书摘
“农民(peasant)”与封建社会(1)一、“农民(peasant)”与封建社会如今的人们不会对“新时代的农民”之类词组感到别扭;仍然断言农民是现代化之弃儿的言论,也比过去少多了。然而无疑,当人们提到农民的时候,更多地还是联想到人类的农业文明时代。在古汉语中,甲骨、金文时代就已分别有了“农”与“民”这两个词,但作为一个词的“农民”则出现得稍晚。《礼记·月令》有“农民毋有所使”句;《春秋谷梁传》成公元年条称:“古者有四民:有士民、有商民、有农民、有工民”;《吕氏春秋》则提到“古圣之重农民”。在这些较早出现“农民”一词的典籍中,“农民”这一概念已经有了职业与身份等级这双重意义:
“农(農)”主要是个职业概念。“農”字下为“辰”,古时指贝壳制的农具,是为意符;上为“曲”,曲古音奴,是为音符。但远古汉语多同音义通,因而曲亦有“奴”义(后之“部曲”、“委曲”诸词仍然保有此义痕迹),于是“农”也就有了身份低下的意思。
“民”主要是个身份概念。“民”,古同“氓”、“萌”,指卑贱的下人。后世无论是贱民、下民、草民、子民等称呼,还是官民、绅民、君民等对举,都显示了“民”的卑下身份。这种身份是传之子孙的。包括“农民”在内的“四民”最初几乎就是四个种姓:“农之子恒为农”、“工之子恒为工”等等。那时绝大多数“民”自然是务农的,于是“民”在很多场合也有了职业含义:“农者,民。”董仲舒:《春秋繁露》卷十三。“农”、“民”成了近义。因而古字书《六书略》作了这样的“解字”:“民:象俯首力作之形”。
清代的《康熙字典》不满意《六书略》的解释,认为“四民兼士农工商,岂力田始称民乎?《六书略》之说,穿凿不可从”。这一批评当然是有分量的。不过如果我们注意到一字可有广、狭、古、近诸义的话,则《六书略》之说也未必为“穿凿”。即如《康熙字典》本身对此亦有旁证,该书“萌”字条曰:“耕亦曰萌”,而古时萌与民通,这是《字典》也提到的。其引《说文》曰:民,“众萌也,言萌(懵)而无识也。”又氓:“《说文》:民也”,“《石经注疏》作甿,甿与氓通。”又《汉书·刘向传》“民萌何以戒勉”条注曰“萌与甿同”。可见,古时民、氓、萌皆训“甿”,而“甿”就是农奴。《周礼·地官·遂人》曰:“凡治野:以下剂致甿,以田里安甿,以乐昏扰甿,以土宜教甿。稼穑:以兴锄利甿,以时器劝甿,以强子任甿。”郑玄注曰:“变民言甿,异外内也。甿,犹懵懵无知貌也。”
可见,尽管从广义、近义而言,“民”为士农工商之总称,但从狭义、古义而言,民(氓、萌)本同甿,指务农的下等人。他们在“田”边“忙”碌,“俯首力作”,而被上等人视为“懵懵无知”、“萌而无识”的贱者。他们以凝固的身份被置于公社之中,致之以“下剂”,安之以“田里”,教之以“土宜”,劝之以“时器”,任之以“强子”。在后世“民”的概念广义化以后,上述“民”的狭义仍然处处可见。如农时被称为“民时”(《国语·齐语》:“无夺民时,则百姓富”),农事被称为“民事”(《孟子·滕文公上》:“滕文公问为国,孟子曰:民事不可缓也”),农兵被称为“民兵”(《玉海》卷一三九《庆历兵录》:“凡军有四:……曰民兵,农之健而材者籍之”),农具被称为“民用”(《国语·周语上》:“民用莫不震动,恪恭于农”,注:“用,谓田器也”),农业被称为“民功”(《国语·越语下》:“不乱民功,不逆天时,五谷睦熟”),等等。而最明显的是在户口管理上,直到明清仍把农籍称为“民籍”。明代有军、民、匠、灶(盐户)诸色户籍,皆世代相袭,不得更易。明时的屯田又有军屯、商屯与民屯之别。这里的“民”非军非商非匠非灶,实专指农户而言。清代亦然,《清会典》卷十七《户部》称:“凡民之著于籍,其别有四:一曰民籍,二曰军籍,三曰商籍,四曰灶籍。”“凡民之别:有民户,有军户,有匠户,有灶户,有渔户。”所谓民籍、民户,即指农籍、农户。农者民也,民者农也,职业概念与身份等级概念混而为一了。
显然,这个意义上的“农民”只能是个前现代的概念。因为现代文明可以有农业这种职业,但不可能有身份等级制。
人们一般用“农民”一词去翻译英语中的peasant(总称peasantry)与farmer两词,这自然只能是近似的:不同文化背景使两种语言中的词汇间难以精确对应。不过西方也有过存在身份等级制的农业文明时代,因而他们的“农民”也是职业概念与身份概念的结合。其中farmer这个词是由farm(农业、农庄)派生的,主要是个职业概念,常与fisher(渔民)、artisan(工匠)、merchant(商人)等职业并列。现代社会中仍有农业,自然也就有farmer,?当今发达国家的农业主要由市场经济中的农场构成,因此在现代语言中,farmer已逐渐含有“农场主”之义了。
用户评价
这本书的装帧设计真是令人眼前一亮,那种略带复古的米黄色纸张,配上烫金的书名,拿在手里就感觉沉甸甸的,仿佛承载着厚重的历史。我尤其喜欢封面那种手绘风格的插图,线条粗犷却不失细腻,描绘的似乎是某种田园风光,但又隐约透出一种超脱现实的、近乎梦幻的笔触。内页的排版也十分考究,字距和行距都处理得恰到好处,长时间阅读下来眼睛也不会感到疲劳。不过,虽然这本书的实体感很棒,但坦白说,我更关注的是它的内容深度。我期待它能在传统史学叙事的框架之外,带来一些耳目一新的视角,那种能够让人沉浸其中、产生强烈代入感的文字,而不是干巴巴的资料堆砌。希望这本书能像它的名字一样,既有田园牧歌式的宁静与美好,又有狂想曲般层层递进、令人振奋的论证结构。总而言之,从物理层面来看,这是一件值得收藏的艺术品,现在就等着内容能够与之匹配了。
评分这本书的语言风格变化幅度非常大,简直像是在阅读一部交响乐谱。有些章节的文字是极其凝练和古典的,用词考究,逻辑链条严密得像瑞士钟表,每一个论点都建立在前一个论点的坚实基础之上,读起来需要全神贯注,生怕漏掉了一个关键的转折词。然而,穿插在这些严谨论述中的,是一些近乎散文诗的段落,尤其是在描述特定历史场景或文化氛围时,作者的笔触变得异常柔软和富有想象力。这些段落充满了感性的色彩,似乎在试图“复原”那些逝去的日常感受,而不是仅仅记录事件。这种文风上的“双轨制”策略,一方面确保了学术的严谨性,另一方面又极大地提升了文本的可读性,避免了陷入纯粹的学术枯燥。我猜想,这大概就是“狂想曲”意象的体现——在严格的曲式结构下,注入无限的即兴与情感表达。
评分初读这本书的引言部分,我立刻就被作者那种近乎偏执的求真精神所吸引。他似乎并不满足于对既有史料进行简单的梳理和诠释,而是执意要从一个完全陌生的角度切入,试图解构我们长期以来习以为常的“前近代”概念。那种叙事节奏,一开始是缓慢而富有韵律的,就像清晨薄雾中慢慢展开的画卷,充满了对细节的捕捉。作者在探讨地方社会结构时,没有直接跳到宏大的政治叙事,而是从具体的家族纹理、土地关系的微观层面着手,这使得整个论证过程显得异常扎实。但随后,他突然转换了一种更为激进的、近乎批判的语调,开始对某些主流历史学派提出挑战,这种急剧的风格转换,虽然在学术上或许是必要的“拨乱反正”,但对于非专业读者来说,阅读体验上会有一点点“陡坡感”。我个人更偏爱他那种沉静地铺陈事实,然后由事实自然引出结论的段落,那才是真正有力量的地方。
评分这本书的结构安排,与其说是线性的时间叙事,不如说更像是一种螺旋上升的辩证过程。每一章似乎都在围绕着一个核心的“悖论”进行深入探讨——比如秩序与混乱的共存,或者保守与变迁的张力。作者不断地抛出问题,然后又用新的材料和更深层次的分析去回应和解构这些问题,这种“问—答—再问—再答”的模式,使得阅读过程充满了智力上的挑战和享受。我感觉自己不是在被动地接收信息,而是在与作者一同进行一场漫长而艰辛的思维探险。尤其是收尾部分,作者没有给出任何过于简化的、一锤定音的结论,而是留下了一些开放性的思考空间,这非常高明。它意味着,历史的研究永无止境,我们所能做的,只是不断地拓宽视野,并对既有的认知保持一种审慎的怀疑态度。这是一部能够让人读完之后,依然久久不能平静、并在日常生活中重新审视周遭事物的作品。
评分我注意到,作者在援引史料时,似乎特别偏爱那些非官方的、民间流传的文本和口述记录,这一点非常合我心意。传统的历史研究往往过于依赖官方文书和宫廷档案,这难免会使得历史的“面孔”变得单一而刻板,只剩下庙堂之上的权谋与礼仪。然而,这本书却努力将我们的目光拉回到那些被边缘化的群体——比如地方士绅、手工业者、甚至一些具有地域特色的宗教实践者。通过对这些“非主流”声音的挖掘和重构,作者似乎在试图还原一个更为立体、充满生命力的前近代社会图景。这种“自下而上”的史学路径,虽然在资料搜集上耗费了巨大的心力,但最终带来的认知冲击是巨大的,它迫使读者重新审视自己对于“传统社会”的刻板印象,比如那个看似铁板一块的宗族结构,在作者的笔下,也变得充满内在的张力和矛盾。
评分好书,教学科研用书,思想深刻,深入浅出,直面问题。
评分一本好书,作者的一本书被禁了,就看看他的其他的了。
评分秦晖老师的代表作,对前近代社会深刻的剖析!
评分活动季购入,非常划算,都是人文社科的专著,口碑良好,对我们相关学习大有裨益,值得收藏。
评分从辩证法角度分析,如何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
评分深论!!!!!!!!!!!!!!!!!!!!!!
评分这是一套有价值的书,印刷不错,纸张挺好,是正版新书,物美价廉,买的很放心。谢谢!
评分期待已久,终于拔草!
评分一部深根于土地,研究中国农村土地与社会发展问题的集大成者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内容均为互联网搜索引擎提供的公开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储任何数据与内容,任何内容与数据均与本站无关,如有需要请联系相关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于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6 book.cndgn.com All Rights Reserved. 新城书站 版权所有


![如何做综述性研究 [Synthesizing Research:A Guide for Literature Reviews]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qciss.net/10040294/c64b1277-47f4-40ba-885a-e27497ef4ff7.jpg)




![高中英语课堂教学设计丛书:高中英语阅读教学设计 [Reflection&Research on Classroom Teaching of English Reading]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qciss.net/11014868/rBEIDE_6izAIAAAAAAE7MEXakcoAADzyAAmBCUAATtI406.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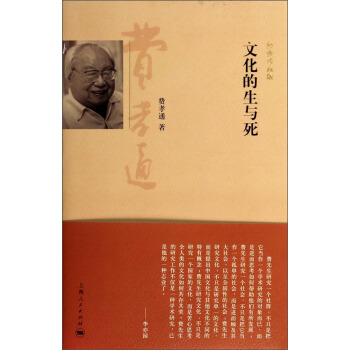


![实用苏州话(中英文对照版)(附光盘) [Practical Suzhou Dialect]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qciss.net/10878103/105b5a1a-0f8c-42e7-a88e-f595e880c8c2.jpg)
![立场 辩证思维训练经济篇(第15版) [Taking Sides-Economic Issues]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qciss.net/11467048/5386eb52Nd5fde65f.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