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具体描述
编辑推荐
《不含传说的普鲁士》:欧洲近代史上迷雾重重的一段传奇,享誉德国三十余年的经典之作。内容简介
普鲁士是一个神话。对某些人来说,它代表着秩序、正直与宽容;对其他人来说,它却集军国主义与反动作风于一身。身为普鲁士人的塞巴斯提安.哈夫纳抛开旧有的传说,娓娓道出这个国家的历史。哈夫纳解释了普鲁士的特殊之处,表明它是一个人工化的产物:普鲁士需要强烈的自保意志,才得以将分散各地的国土凝聚成一个相互连贯的整体。在数百年的演进过程当中,普鲁士是由民情迥异的德意志与斯拉夫殖民地区共同生长而成,缺乏共通的血源或宗教基础、没有天然的疆界,以致它只能说是一个“理性国家”。廉洁的政府以及对宗教的宽容,使得普鲁士成为十八世纪欧洲比较现代化的国家。它的危机閞始于法国大革命,它在建立德意志帝国之后陷入缓慢的死亡,国家社会主义则促成普鲁士的毁灭。
哈夫纳探讨这个不寻常的国度时,心中不存偏见、抱持批判态度,但不无钦佩之意,使得这本《不含传说的普鲁士》成为一部关于普鲁士历史的独特著作。
作者简介
塞巴斯提安?哈夫纳 | Sebastian Haffner,1907年生于柏林,逝于1999年;法学博士,被普遍认为为是20世纪德国历史重要的时代见证者。1938年与犹太裔未婚妻移居英国担任记者。1954年以英国《观察家报》海外特派员的身份重返德国后,自1961年起先后为德国《世界报》《明星周刊》撰写政论专栏。著有一系列以历史为主题的畅销书,包括《解读希特勒》《从俾斯麦到希特勒》《不含传说的普鲁士》。目录
地 图(8幅)译 序:黑中有白,白中有黑的普鲁士
导 言
第一章 漫长的成形过程
东向殖民的三种模式
霍恩佐伦家族的权力政治
大选侯的悲剧
普鲁士王国得名的由来
第二章 粗线条理性国家
两位伟大的国王
一场军事革命
君主政体与容克贵族制度
普鲁士的三个无所谓
第三章 微不足道的强权
有利的大环境
腓特烈大帝的冒险
一位受到低估的普鲁士国王
普鲁士成为双民族国家
第四章 严峻的断裂测试
一位爱好和平的国王
一场莫名其妙的战争
改革与反改革
普鲁士的西移
第五章 三只黑色的老鹰
不一样的普鲁士
复辟与反动
普鲁士与“德意志联盟”
在奥尔米茨的投降
第六章 普鲁士建立帝国
俾斯麦一世国王
政治权谋与成功压力
一八六六:普鲁士成功达阵
一八七○:一场意外与一个即兴创作
第七章 缓慢的死亡经历
国家意识上的革命
普鲁士的撤退战
一个没有人要的国家
普鲁士的毁灭
年 表
前言/序言
译 序黑中有白,白中有黑的普鲁士
吾乃普鲁士人,你可知我颜色?
黑白旗帜在我面前飘扬;
吾列祖列宗为自由而牺牲,
请谨记,这是我颜色的真谛。
我永不畏葸退缩,愿与先人一般果敢,
无论天色昏暗或阳光普照,
吾乃普鲁士人,愿为普鲁士人!
—普鲁士国歌
曾经翻开过《一个德国人的故事》、《破解希特勒》、《从俾斯麦到希特勒》等等哈夫纳论述的人,往往对封面内页提到的《不含传说的普鲁士》一书颇感好奇。结果这本关于普鲁士的经典著作,在过去几年成为「左岸出版社”被询问度最高的书籍。如今它终于也和读者朋友们见面了。对译者自己来说,本书更具有非比寻常的意义:当初我透过它而开始私淑德国政论大师哈夫纳先生、它是我德国史—尤其是普鲁士史—的启蒙书之一,并且陪伴我完成在德国的学业。《不含传说的普鲁士》这个标题,则甚至早在开始翻译本书整整三十年前即已出现。
讲得精确些,事情要回溯到一九八○年底,译者留学西德半年之际。某天我在杂志上看见一本精装版新书的广告,不禁深受吸引。一方面是因为其标题—《Preusen ohne Legende》—十分简洁别致,几乎让人不知该如何翻译才好(光从字面来看,它叫做「普鲁士没有传说”)。另一个理由则是,我们小时候都在历史课本里面读过:「一八七一年,普鲁士铁血宰相俾斯麦统一了德国”—「俾斯麦”是人人皆可琅琅上口的对象,「普鲁士”一词却容易让人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普鲁士到底是什么?普鲁士位于何方?谁是普鲁士人?俾斯麦统一德国后,普鲁士又跑到哪里去了?……但最令人纳闷的当然还是:此处的「传说”究竟所指为何?
可惜精装书很不便宜,再加上译者当时正为了准备「下萨克森邦”(昔日普鲁士「汉诺威省”)的「拉丁文执照考试” 而忙得焦头烂额,所以只是把「普鲁士没有传说”挂在心上,继续纳闷下去。时至一九八一年夏天,我总算顺利通过考试得以正式展开学业,于是订购了那本普鲁士专论来犒赏自己,并前往普鲁士的故都柏林市,不但参观西柏林举办的普鲁士特展,还去东柏林游玩了一天。 我从西柏林坐地铁进入东柏林之后,一离开车站便不知不觉步行来到著名的「菩提树下大街”,赫然看见理论上不该出现的东西:那里巍巍矗立一座纪念碑,顶端安放一尊巨大铜像,刻画出一位身穿戎装、头戴三角帽的骑士。那是腓特烈二世国王(「大帝”),普鲁士的标竿人物!东德这个社会主义“民主共和国”首都精华地段最主要的道路旁边,竟堂而皇之陈列一尊「封建君主”骑马立像,未免令人匪夷所思。
当初东德在一九四九年建国之后,第二年就把位于东柏林的普鲁士王宫和「德皇威廉一世纪念亭”拆得一乾二净,藉以彻底清除「反动的普鲁士军国主义”之遗迹。腓特烈纪念像的底座也被大卸八块移走,铜像本身则险些毁于熔炉,幸好后来法外开恩,仅仅把它发配至波茨坦的一座花园。到了一九八○年十一月底(就是译者看见「普鲁士没有传说”广告的差不多同一时候),东德共党政府作风丕变,又大费周章将之迎回「菩提树下”!
东柏林的普鲁士国王铜像消失三十年后蓦然重返,西柏林则大张旗鼓举办普鲁士特展,显然译者恰好躬逢其盛,现场目睹东西柏林如何重新发现了普鲁士,并且竞相透过普鲁士来面对自己的过去。不过双方跨出这一步的时候都需要很大勇气。毕竟之前的情况相当敏感,而那可以套用东德末代总理和第一位民选总理—德.梅西尔—的讲法说明如下:东西两个德国都曾经是盟军一九四七年一项决议的执行者。东德的代表人物是「一九四九世代”,将「普鲁士精神”斥为「法西斯独裁政权的重要基础”;西德则有「一九六八学运世代”,把「普鲁士的价值观和美德”贬低成「蔑视人性”。
自从德国于一九四五年战败、覆亡和遭到占领以来,普鲁士便成为禁忌。德.梅西尔所指出的那项「决议”,其实是美、苏、英、法四国引申丘吉尔「普鲁士乃万恶之源”的论调,给普鲁士开立的「死亡证明”。纽伦堡大审结束四个多月后,「盟军管制委员会”在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五日签署《第四十六号法令》,宣布「普鲁士国家历来是德国军国主义和反动作风的支柱,它事实上已经不复存在”,为求「维护各民族的和平与安全”,以及「在民主基础上进一步重建德国的政治生活”,自即日起「解散普鲁士”。
看来普鲁士会让人气愤得做出「激烈反应” ,甚至「陷入矛盾”。既然普鲁士已不复存在,「盟军管制委员会”又怎能「解散”(或「废除”)那个不存在的东西呢? 不过此一怪异事件已让人初步领略普鲁士的「传说”色彩:它是一个拥有「死亡证明”的国家,生前既「不民主”又「危及各民族的和平与安全”,却足以令东西柏林同时对它缅怀不已,而且它还具备某些「美德”……。于是译者在一九八一年夏末从西柏林返回我那所位于东西德边境的大学后,立刻开始仔细阅读刚买来的精装书,这才化解心中的疑惑,终于明白书中所强调的并非「普鲁士没有传说”,而是普鲁士被硬生生套上了五花八门的「传说”,以致充满着「神话”、「迷思”与「扭曲”。
普鲁士国旗只出现黑白两种颜色(起初甚至没有黑鹰图案,光是上黑下白),而那些「传说”就跟普鲁士的旗帜一样黑白分明,结果喜欢普鲁士的人只看见白色(如「秩序”、「正直”与「宽容”),不喜欢普鲁士的人只看见黑色(如「好战”、「反动”和「不民主”),德国人则要等到一九七○年代,才打破禁忌来正视普鲁士「白”的一面。哈夫纳就在整体氛围出现微妙变化的时刻,以普鲁士人的出身、批判的态度和不存偏见的做法,探讨了那个不寻常的国度。既然哈夫纳的着眼点是要破除神话与迷思,于是我在一九八一年秋季决定,干脆把书名称作《不含传说的普鲁士》好了。谁知时隔三十年后,它成了本书中译版的正式标题。
* * *
普鲁士最为人诟病之处和各种传说的根源,无疑是其军国主义。现在就让我们看一个军事方面的统计数字: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二世在一七四○年五月登基时,他的父亲(「士兵国王”腓特烈.威廉一世)留给他一支八万三千人的军队—当时普鲁士已将近三十年没打过仗了。
对面积为台湾三点三倍的国家来说, 八万三千人的常备兵力似乎不多。然而普鲁士当时总共才二百二十万人,因此军人占了国民的百分之三点八。这看起来也还正常,但继续计算下去的话,我们只会得出十分耸动的数字:其情况相当于美国在承平时期养兵一千二百万,或者中国和印度随时维持五千万大军!更骇人听闻的是,普鲁士那年的军费支出高达全国岁入的百分之七十二点四,随后数十年内更动辄超过百分之八十!若在别的国家,这种国防开销恐怕早就把经济拖垮。 一七四○年时的普鲁士却同时握有「完成战备的部队”和「装得满满的国库”,以致腓特烈二世在同年年底放胆出兵夺取奥地利的西里西亚,结果战争时断时续地进行到一七六三年。最后普鲁士同时跟欧陆最强大的法、奥、俄三国鏖战七年,打成了平手。莫非普鲁士天赋异禀?
那倒未必,不过普鲁士人的确具备许多美德,而美德往往源自「迫于无奈”或「后天养成”。想明白这点,我们不妨翻阅一下书中附上的几张地图。
一九八一年译者首度看见它们时,浮现的第一个印象是「怎么好像在下围棋?”因为那些土地互不相连,从荷兰、瑞士一直散布到立陶宛和波兰。「棋盘”的重心在易北河东方,而那里起先主要只有「布兰登堡边区”和「普鲁士公国”两个不相干的国度:前者是神圣罗马帝国的边陲之地,乃十二世纪「东向殖民”创造出来的结果; 后者则为十三世纪「条顿骑士团”所建立国家的残余部分,在十七世纪中叶成为自主国。历史的因缘际会,使得布兰登堡边疆伯爵在三十年战争爆发那年(一六一八年),开始兼任普鲁士公爵。「布兰登堡—普鲁士”不仅诞生于战争中,瑞典和神圣罗马帝国军队的来回肆虐,更导致布兰登堡边区损失了三分之一以上的人口。
等到三十年战争终于结束后,那个地寡人稀的国家开始创建常备军来自卫。军队虽然主要只使用为谈判时的筹码,但随着军备规模的不断扩大,财政负担日益沉重,迫使普鲁士全国上下必须以最务实的态度,做出最合理的规划、最具效率的措施,以及最精确的行动—我们大可将此简称为「穷人的俭朴美德”。哈夫纳在本书第二章,便对此做出非常精彩的叙述,说明「国家自保本能”和「国家利益至上原则”,如何鞭策普鲁士在十八世纪那个崇尚理性主义、启蒙运动和开明专制的年代,逐步成为欧洲国家之典范,甚至成为全欧洲受迫害者的庇护所。那些来自欧洲各地的人才,又在工商业、科学和文化上带来了进步。十八世纪初的时候,柏林市的人口甚至三分之一来自法国,而且他们一直留了下来,例如东德末代总理德.梅西尔就是昔日法国难民的后裔。
一七○一年一月十八日,布兰登堡—普鲁士的统治者做出一个「借壳上市”的动作,在不属于神圣罗马帝国的普鲁士公国加冕为国王,其辖下宛如由一群变形虫组成的国家从此更名为普鲁士王国。此「借壳上市”之举具有两层意义。首先,布兰登堡边区形同将自己位于帝国内部的领土「转移到境外”,从此更方便名正言顺地跟帝国打对台。从另一方面来看:东向殖民者刚越过易北河的时候还是日耳曼人,但他们很快就在血源上融合成为一个半日耳曼、半斯拉夫的民族—古普鲁士人却是跟他们格格不入的「野人”,使用一种让日耳曼人和斯拉夫人都听不懂的语言。换句话说,那些「新普鲁士人”决定把「异族”的名称使用为共同的国号!
这让人再度回想起普鲁士国歌的歌词:「吾列祖列宗为自由而牺牲”可烘托出普鲁士努力让国家在帝国旁边自由活动。就「无论天色昏暗或阳光普照”而言,军国主义岂不像是太阳,同时映照出普鲁士阴暗与光明的一面,逼迫普鲁士既「侵略成性”又「充满美德”?至于「普鲁士”这个「借壳上市”的国号,不正是「愿为普鲁士人”之最佳体现?
由于普鲁士王国并非民族国家,其疆域支离破碎,各地民情差异颇大,「愿为普鲁士人”便意味着认同一种特定的生活方式。若按照普鲁士哲学家康德的讲法,那叫做「只按照……能成为普遍规律的准则去行动”。特殊的历史和地理条件,再加上军事压力、财政负担和政治需求,促成普鲁士的「国家利益至上原则”结合了「启蒙运动精神”与统治者的「新教伦理”,创造出所谓「普鲁士美德”, 大致为:诚实、自制、纪律、勤奋、服从、直率、公正(各得其所)、虔诚(但宗教宽容)、刚直(严于律己)、勇气、守秩序、责任心、精确、正直、无私忘我、节俭、无畏(不自怨自艾)、忠诚、廉洁、谦逊、开明、实质重于表象、可靠。由于普鲁士最后统一了德国,而且德国三分之二的地方直接归普鲁士所有,那些「普鲁士美德”多半进而成为一般人印象中「德国人的美德”。
固然不可能人人具备这些美德,但普鲁士国家理念可以此为标准来形塑国家的统治者和国民,让他们共同替一位抽象的「普鲁士国王”效力。上述美德又可总结成「铁的纪律”、「强烈的责任心”与「高度的服从性”,而其成效有目共睹:普鲁士在极短时间内,便从穷乡僻壤跃居欧洲五强之一。地理因素虽使得普鲁士成为「肉食动物”,必须不断向外扩张和推动土地调整政策,否则国家疆域连形状都没有。但普鲁士通常却宁愿只当「食腐动物”,在谈判桌上和平继承别处的土地,甚至表现得仅仅像是「刺猬”一般。军队往往只是最后的手段,能不出兵就不出兵,因此普鲁士在历史上经常连续偃兵息鼓几十年,不像英法俄老是在某地动武。但普鲁士不打仗则已,一打起来就轰轰烈烈,于是给人一种「特别好战”的感觉。其实除了腓特烈二世的西里西亚战争、一八一三年反拿破仑的「解放战争”,以及一八六四至一八七一年的三场战争,普鲁士打过的仗并不多。
十九世纪的普鲁士再也无法随心所欲自由行动。它先是被拿破仑击败而沦为法国附庸,接着又融入梅特涅的欧洲体系,并且与奥地利和俄国结成「神圣同盟”,在一八四八革命之前成为对抗民主运动和民族运动的急先锋。结果十八世纪那个理性十足,既进步又宽容的模范国度,变得既反动又充满向往中世纪的浪漫主义作风,普鲁士国王则始终未能走出开明专制的阶段。等到梅特涅体系崩溃后,普鲁士继续跟着新的时代精神齐头并进,可惜时代精神已变成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结果普鲁士遭到德意志民族主义绑架而走上悲剧之路。
普鲁士统一德国的行动,到头来只意味着一种「最光荣的退场机制”—大多数普鲁士人从此「愿当德国人”,而且往往变成狂热的德意志民族主义者。俾斯麦终于让普鲁士「吃饱了”,不必再进行扩张。普鲁士却逐步迈向死亡,被另外一个饿肚子的国家(德意志国)取而代之。普鲁士军队已转轨成为德国军队,只向德皇或「元首”个人宣誓效忠。在德皇威廉二世那个狂妄自大的时代,德国社会已全面军国主义化,几乎到了「只有穿军装的人,才算得上是人”的地步。而就在普鲁士早已名存实亡之际,普鲁士「黑白传说”却如雨后春笋一般不断冒出,而且黑色逐渐压过了白色;白色的传说则往往沦为极右保守派的宣传工具。等到希特勒上台的时候,普鲁士已在半年前死于「普鲁士政变”。希特勒却滥用了普鲁士人美德,将从前知所节制的「肉食动物”改造成纪律严明、责任心强、高度服从的「掠食动物”,制造出千古浩劫。
其实不光是普鲁士,就连德国也因为希特勒而永远留下了污名。可是把希特勒的帐全部都算到普鲁士和德国头上,则未免有欠公允。我们读完《不含传说的普鲁士》以后,或许更可体会德.梅西尔以“法国胡格诺血统的普鲁士人、具欧洲色彩的德国国民、世界公民与基督徒人道主义者”之身分说出的话:“把普鲁士缩减成‘军国主义’与‘反动作风’的做法,就和把最近四百年来的德国历史缩减成十二年(纳粹德国)的做法一样不合理。”
周 全
二○一二年三月于台北
写于普鲁士腓特烈二世国王诞生三百周年纪念
用户评价
我得说,这本书的阅读体验是相当“反直觉”的。通常我们阅读历史,总期望能找到清晰的因果链条或戏剧性的转折点,但《不含传说的普鲁士》却提供了一种近乎散点透视的阅读感受。作者似乎刻意避开了那种引人入胜的叙事高潮,转而用大量详实、甚至枯燥的资料和档案片段来构建他的论点。这需要读者具备极大的耐心和专注力。我尤其欣赏它对“法律与秩序”这种看似中性的概念进行深度解构的方式。它不是在批判法律的残忍,而是在展示法律体系本身是如何作为一种自我完善的逻辑实体而存在的,它不需要外部的道德审判,仅仅依据其自身的规则运行,并因此产生了巨大的社会惯性。这种“去情感化”的写作风格,初读时会让人感到一丝疏离和寒冷,仿佛在阅读一份冰冷的政府报告,但随着阅读深入,你会意识到,正是这种冷静,才使得书中的分析具有了无可辩驳的力量感。它让你明白,强大的结构往往不是靠激情维系的,而是靠无数次无聊的、重复性的合规操作堆砌而成。
评分坦白讲,初接触《不含传说的普鲁士》时,我曾担心它会变成一部晦涩难懂的学术专著,充斥着我并不熟悉的德语术语和历史人名。但作者的叙述技巧非常高明,他巧妙地将那些原本散落在不同领域的碎片信息编织成一张网。有趣的是,这本书很少直接下判断,它更像是一位建筑师在展示蓝图——他精确地标明了每一根承重梁的位置、每一块砖石的材质,至于这座建筑最终给居住者带来的是安全感还是压抑感,则留给读者自己去体会。我印象特别深的是他对19世纪中后期普鲁士“公民意识”的描绘。那不是一种基于自由平等的权利意识,而是一种建立在“责任与义务”之上的义务感,这种义务感是如此根深蒂固,以至于人们在享受秩序带来的好处时,也心甘情愿地接受了被规训的命运。这本书真正做到了“不含传说”,因为它没有试图赋予这些历史人物或事件以我们现代人所期待的道德光环或戏剧性光芒,它只是陈述了一个高度组织化社会的运作机制。
评分这本书给我的最大启示是,历史的重量并不总是在于那些轰轰烈烈的事件本身,而在于那些被视为理所当然的、习以为常的基础设施。阅读《不含传说的普鲁士》的过程,与其说是在回顾一个过去的国家,不如说是在审视我们自身社会结构中那些被我们忽略的、坚硬的内核。《不含传说的普鲁士》像一剂清凉的药,它冲刷掉了所有关于浪漫、英雄主义或民族宿命论的色彩,剩下的只有冰冷的、可供分析的社会工程学样本。我尤其喜欢其中探讨的“精英的自我隔离”现象——那些制定规则的人,似乎也成为了被自己规则所困住的第一个群体。这种讽刺的意味,是随着你对全书内容的理解加深而逐渐浮现的,并非一开始就昭然若揭。它不是一本适合在睡前放松时阅读的书,它要求你保持清醒,去辨认那些潜伏在看似高效运转背后的巨大代价。读完后,我感觉对任何宣扬“绝对秩序”的理念都会更加警惕和审慎。
评分这本书最让我感到震撼的地方,在于它对“实用主义”的彻底贯彻及其对文化想象力的扼杀。许多关于普鲁士的论述,都会提到其强烈的军事化色彩,但作者在这本书里更深入地挖掘了这种军事思维如何演变成一种全民的生存范式,即使在和平时期也是如此。它不是关于“如何打仗”,而是关于“如何组织生活”。例如,书中对城市规划、教育体系甚至礼仪规范的描述,无不闪烁着“目标导向”的理性光芒。然而,这种理性缺乏弹性,缺乏对“无用之美”的容忍。我感觉自己仿佛被拉进了一个巨大的、运转精密的时钟里,每一个部件都必须完美契合,多余的摆动被视为效率的损失。这绝不是一个浪漫或充满人情味的故事,它探讨的是效率的边界,以及当一个社会将效率推向极致后,其内部产生的形而上的空虚感。这种对结构性思维的解剖,比单纯控诉某一任君主或某一场战役的失败要来得深刻得多,因为它直指系统本身的内在逻辑。
评分这本《不含传说的普鲁士》的书名,乍听之下就带着一种令人耳目一新的“反向营销”意味。我带着一丝好奇心翻开了它,期待着能看到一些被历史叙事反复强调的刻板印象的彻底颠覆。然而,出乎意料的是,这本书并非那种激进的“打脸”历史著作,它更像是一位老练的、近乎冷酷的观察者,用一种近乎手术刀般精准的笔触,剖开了那个被神化或妖魔化的国家肌理。它没有沉溺于腓特烈大帝的军事天才或俾斯麦的铁血手腕这些“硬通货”传说中,而是将聚光灯投向了日常生活的微观层面,那些构成国家运作的无数个齿轮——从晦涩的行政法规、僵化的官僚体系,到小市民在严苛社会结构下的精神状态。它细腻地描绘了普鲁士人那种近乎病态的效率追求如何渗透到家庭伦理和个人信仰中,展现了一种制度对人性的微妙异化。读完整本书,我发现自己对“普鲁士精神”的理解不再是宏大叙事下的单一标签,而是成了一种复杂、甚至有些压抑的生存哲学。这种不带感情色彩的白描,比任何带有褒贬色彩的评论都要有力得多,因为它迫使你直面那个被“传说”掩盖下的真实结构。
评分买书就选京东618,平时性价比不高的刚需书,这时顺手拿下
评分京东的送货速度太快了。
评分好薄一本,居然这么贵?看看的说
评分好书好书,非常满意的一次购物体验
评分豆瓣评价极高 值得购买观赏
评分快递很快服务态度也很好包装无破损。好评
评分包装挺好,没有破损,排队等开
评分很辛苦,只为给客户最优质的服务!
评分普鲁士后来之所以统一了德意志,最终成为小德意志的德国,包含了俾斯麦,最衰败于威廉二世之手也算是咎由自取吧。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内容均为互联网搜索引擎提供的公开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储任何数据与内容,任何内容与数据均与本站无关,如有需要请联系相关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于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6 book.cndgn.com All Rights Reserved. 新城书站 版权所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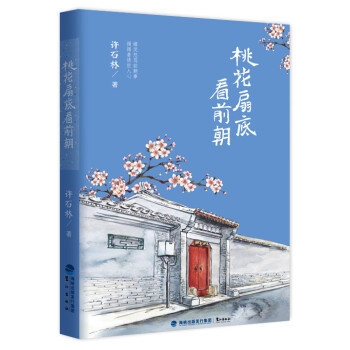







![紫禁城(2015年第二期,总第241期) [Forbidden City]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qciss.net/11666588/5525dc01N3866c6b0.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