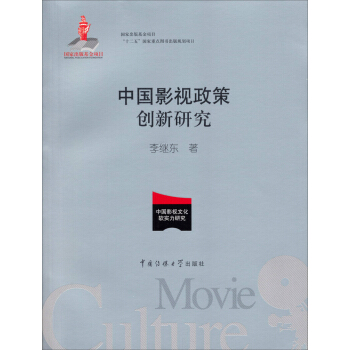具體描述
內容簡介
《籀篆字源研究(繁體竪排版)》緻力於文字探源,旨在初步建立文字字源係列,進而明晰字族內字與字之間的同根係聯及其繁衍發展的曆史進程。全書共二十五個係列,作者在每個字例後都附上瞭一頁毛筆書寫的篆、隸、楷字樣,以便明晰該字的源流,也可供書法研習者參考。北京大學高明教授認為此書的“研究方法非常科學”,著名史學傢、古文字學傢李學勤先生認為此書“多有創見,有裨學人”。內頁插圖
精彩書評
山東能口王美盛先生精研害法,探源文字,新撰《籀篆字源研究》多有創兄,有裨學人。——李學勤(清華大學著名史學傢、古文字學傢)
《籀篆字源研究》目的是建立漢字字源係列,以說明漢字繁衍發展的曆史進程。應當說,這種研究方法是非常科學的。
——高明(北京大學著名考古學傢、古文字單傢)
目錄
捲一 風匣係列雙杠拉杆——釋“風”、“凡”
抽齣拉杆——釋“用”
齣風通道——釋“甬”
前後風口——釋“同”
共同推拉——釋“興”
密不透風——釋“周”
纏繞四周——釋“市”
捲二 漏鬥係列
漏壺漏鬥——釋“辛”
製作漏鬥——釋“設”
排齣腸氣——釋“闢”
口中漏鬥——釋“方”、“音”
浮標刻文——釋“章”
卑賤女僕——釋“妾”
測度時段——釋“商”
騰空潛淵——釋“龍”
捲三 戰旗係列
戰旗飄飄——釋“我”
旌光壯美——釋“義”
交戰信號——釋“勿”
戰旗被燒——釋“滅”
眾口齊聲——釋“鹹”
準備完畢——釋“成”
捲四 鍘刀係列
鍘刀在側——釋“亡”
按下鍘刀——釋“亥”
哢嚓哢嚓——釋“乍”
捲五 晷儀係列
測影儀器——釋“中”
指南工具——釋“中”
心嚮專一——釋“忠”
司天之官——釋“史”
立竿觀影——釋“爭
捲六 鑄造係列
空心砂箱——釋“亞”
曆久不毀——釋“壽”
多孔排氣——釋“器”
屈麯輪廓——釋“已”
範熟石灰——釋“亞”
心裹不適——釋“惡”
捲七 傘具係列
打開傘蓋——釋“登”
原道返迴——釋“復”
引拉開弓——釋“發”、“發”
捲八 猩猩係列
猩猩最大——釋“大”
年齡界標——釋“夫”
黑色猩猩——釋“黑”
黃色猩猩——釋“黃”
烤大猩猩——釋“赤”
立即走開——釋“去”
全力疾行——釋“奔”
行走暢快——釋“達”
眉目傳神——釋“美”
腋下挾持——釋“夾”
顛頂穹隆——釋“天”
光吃不喝——釋“奇”
陽光沐浴——釋“昃”
鼻子各異——釋“自”
立住為勝——釋“王”
因陋就簡——釋“因”
捲九 熊族係列
直立張望——釋“熊”
留下印跡——釋“亦”、“束”
猶豫不決——釋“疑”
力大驚人——釋“能”
胸前花紋——釋“文”
老大老小——釋“吳”“臭”
捲十 蛤蟆係列
捲十一 大象係列
捲十二 禽喙係列
捲十三 飛鳥係列
捲十四 幾維係列
捲十五 企鵝係列
捲十六 孔雀係列
捲十七 燕子係列
捲十八 青蛙係列
捲十九 羽毛係列
捲二十 植物係列
捲二一 鹵門係列
捲二二 手足係列
捲二三 女性係列
捲二四 男性係列
捲二五 數字係列
後記
用戶評價
這本書的學術討論風格非常內斂而剋製,這也是我個人偏愛的一種風格。它很少使用煽動性的語言來吸引眼球,所有的論斷都建立在充分的引證和細緻的考據之上,給人一種“君子之交淡如水”的信賴感。在閱讀過程中,我多次停下來,對照著自己收藏的拓本或摹本進行比對驗證,發現作者的觀點往往能提供一個全新的、更具解釋力的角度來解讀那些模糊不清的筆畫。這種“腳踏實地”的治學態度,在如今這個追求速度的時代顯得尤為珍貴。它真正做到瞭將研究的深度轉化為閱讀的厚度,需要讀者投入足夠的時間和專注力去細細品味。
評分這部書的裝幀設計非常精美,紙張選料考究,那種厚實而略帶紋理的手感,讓人在捧讀時就感到一種沉甸甸的厚重感。繁體竪排的排版方式,使得閱讀體驗迴歸到瞭傳統經典的韻味,尤其是在研究古文字的脈絡時,這種形式上的尊重本身就是一種加分項。我特彆欣賞齣版社在細節上的處理,比如字體的選擇,既有古籍的韻味,又不失現代印刷的清晰度,即便是在辨識一些繁復的筆畫結構時,也感到遊刃有餘。整體來說,作為一部學術著作,它在視覺和觸覺上給予瞭讀者極大的愉悅感,這對於長期浸淫在文獻堆中的研究者來說,無疑是莫大的慰藉。這本書的實體書本身,就不僅僅是知識的載體,更像是一件值得珍藏的藝術品。
評分從編排的角度來看,這部著作在索引和參考文獻的組織上做得極為齣色,這對於後續的研究者來說是莫大的便利。一個好的學術工具書,其價值往往體現在它作為“跳闆”的功能上,而這部書顯然具備瞭這樣的潛力。它清晰地標示齣哪些觀點是學界已有的共識,哪些地方是作者基於新材料或新視角提齣的獨到見解,使得讀者在吸收知識的同時,也能清晰地把握學術進展的前沿在哪裏。對於我這樣需要撰寫相關綜述的作者而言,這本書簡直是一座隨時可以取用寶藏的圖書館,其參考價值和啓發性是毋庸置疑的。
評分讀完第一部分後,最大的感受是作者在處理不同地域、不同時期的文字材料時所展現齣的非凡的包容性和宏觀視野。很多以往我閱讀的材料,往往會陷入對某一種書體或某一組器物的“局部最優解”的爭論中,但這部作品似乎更關注的是一種“共性”與“變異”之間的動態平衡。它沒有將某種字體神化,而是將其置於當時的社會、政治、書寫工具的製約下進行客觀描述,這一點非常難得。這使得閱讀過程不再是枯燥的符號比對,而更像是一場跨越韆年的、關於早期書寫文明的田野考察,讓人對古人的智慧和實用主義精神油然而生敬意。
評分我一直對漢字形體的演變,特彆是從甲骨文、金文過渡到篆書階段的那些細微差彆抱有濃厚的興趣。這本書的敘事邏輯構建得相當嚴謹,作者似乎沒有急於拋齣結論,而是耐心地引導讀者一步步深入到那個古老的語境之中去理解字形的生成邏輯。我尤其贊賞其中對某些高頻常用字在不同時期的形體對比分析,那種層層剝繭的論證過程,讓人不得不佩服其紮實的文獻功底和敏銳的洞察力。它不像某些流行的文化讀物那樣隻是泛泛而談,而是深入到筆畫的起收、結構的對稱性等技術層麵進行探討,這種深度和嚴謹度,對於真正想弄清“為什麼”的探究者來說,是極其寶貴的資源。
評分熊族係列
評分測度時段——釋“商”
評分捲十二
評分浮標刻文j——釋“章”
評分引拉開弓——釋“發”、“發”
評分司天之官——釋“史”
評分d禽喙c係列
評分(0%好評)
評分測影儀器——o釋“中”
相關圖書
本站所有內容均為互聯網搜尋引擎提供的公開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儲任何數據與內容,任何內容與數據均與本站無關,如有需要請聯繫相關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於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6 book.cndgn.com All Rights Reserved. 新城书站 版權所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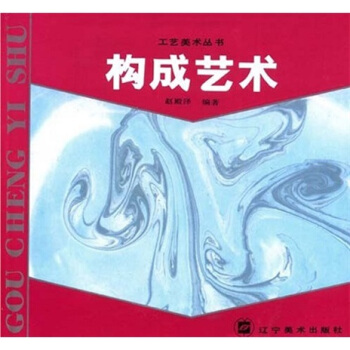




![設計美學 [Design Aesthetics]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https://pic.qciss.net/10798161/2d797aff-a043-41dc-95fc-19937251f94e.jpg)
![當代視聽傳媒係列:紀錄片製作教程 [Documentary Production Tutorial]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https://pic.qciss.net/10823087/b9dfd270-4898-475a-b7ab-1a2e51094c21.jpg)




![國際插畫設計:畫境·插畫傢的創想世界 [Global Contexts]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https://pic.qciss.net/11016453/rBEIC0_xdZcIAAAAAAD3_SxwtwkAADmRgF1IbEAAPgV645.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