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棱镜精装人文译丛·断片集:冷记忆(1991-1995) [Jean Baudrillard Fragments]](https://pic.qciss.net/11194952/rBEQWFFZURQIAAAAAAopZitpvGQAADQcAOuvfMACil-629.jpg)

具体描述
编辑推荐
片段的文字其实就是民主的文字。每个片段都享有一种同等的区别。最平凡的文字却能找到非凡的读者。每个人都会轮流获得权利,以享受自己那光荣的一刻。当人们拥有思想之时,他们大多数人都会变成自己思想的寄生虫。
我们生命的终结是一本崇高的书籍;
人们无法随意地将其合上或是打开;
人们想要保存那些自己喜欢的书页;
但是最后一页已经在我们指尖凋谢;
幻觉是一种更为巧妙的现实,这个巧妙现实以其自身的消失给幻觉披上现实的外衣。
内容简介
《棱镜精装人文译丛·断片集:冷记忆(1991-1995)》精选自波德里亚写作《终结的幻想》和《完美的罪行》期间的笔记,其话题涉及欧洲与东欧阵营,澳大利亚与纽约,艺术与科学,生命与宇宙,虚无与意义……无论是对自然演变的反思还是对社会进程的洞见,是沉默的智慧还是犀利的批判,皆充满了诗意的冥想与凝练的光芒。作者简介
让·波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1929-2007)法国哲学家、社会学家、后现代理论家。先后任教于巴黎十大和巴黎九大,其著作分析当代社会文化现象,批判当代资本主义,具有广泛的世界性影响。主要代表作有《物体系》《消费社会》《生产之镜》《象征交换与死亡》《论诱惑》《美国》《完美的罪行》及系列随笔《冷记忆》等。张新木,江苏高淳人,南京大学法语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副院长、中国驻法国大使馆教育处一等秘书。1985年起从事符号学研究,翻译出版法国文学与社科名著《巴黎圣母院》《游荡的影子》《冷记忆》(1-5)等30余部,主持建设国家精品课程“法语阅读”。2006年获法国政府棕榈教育勋章(骑士),2008年获江苏省第三届紫金文学奖翻译奖。
陈晏乐,浙江永康人,南京陆军指挥学院国际军事教育交流中心讲师,教译二室副主任。主要从事跨文化传播研究,参与翻译法国文学作品《圣艾克絮佩里作品集》及外军留学生教材10余部。
李露露,贵州贵阳人,南京陆军指挥学院国际军事教育交流中心教员。主要从事法国文学和军事理论的研究,参与翻译出版法国社科译著《无边的艺术》及外军留学生教材3部。
内页插图
精彩书摘
人们很快就会转向反对医学的斗争,而不是与自身的疾病进行斗争。最终只有通过对医学的精神发泄,通过对既能保护又生恐怖的医学器械的发泄,人们才能不经其他任何形式而治愈疾病。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医学是无法回避的。也许医学本身就从巫术中承袭了这种转移疾病的倒错功能。只要(海湾)战争还在继续,看守部级机关大门的保安们就依然宽容大度,而一旦风险排除后,他们就变成了严格的执法者。
当一种功能变得无用时,就越是要加强,这是很正常的事。因此,官僚主义长期以来就是一种过分强化(而又恼人)的功能。同样,广告也以自嘲的方式、反广告和反话的方式加强自己,很久以来,它已经不知道应该遵循什么功能。因此,当其目的烟消云散时,性欲却越来越强(当结果消退时,欲望便在膨胀)。
因此,抗体也开始发作,启动了自身免疫系统的各种疾病,因为它们意识到,在一个受到超级保护的身体内,自己已无用武之地。他们也像那些保安一样,要挽回他们那龙套角色的尊严。
在录音室里,你的思绪犹如在讲词提示器上一一而过,你变成了你自己思想的自动读者。尤其是当你的目光碰巧落在了控制屏幕上时,你就能看见你正在实时中讲话。
在电视摄影厅里,你会感到你的思想正在失去其精神,失去某种品质,人们只能在诱惑或竞争的关系中找到(如果能找到的话)这种品质。人们只有在相异性中才具有精神,即使这些思想处在孤独中亦然。
……
前言/序言
用户评价
“棱镜精装人文译丛”这个系列的出现,本身就代表着一种对深度和品质的追求。而《断片集:冷记忆(1991-1995)》作为其中的一员,其沉甸甸的体量和精美的装帧,已经足以吸引我。鲍德里亚,这个名字对于任何一个对后现代思潮有所了解的人来说,都意味着一场思想的风暴。他的哲学常常是一种颠覆性的,挑战着我们习以为常的认知模式。我尤其对“断片集”这个形式感到好奇。不同于系统性的理论著作,断片化的表达方式,往往更能捕捉到思想瞬间的灵光,或是那些难以被逻辑串联起来的直觉。我想象中的“冷记忆”,或许是他对当时社会现象、文化潮流、甚至是一些哲学思辨的零散记录,这些记录虽然彼此独立,但却可能在某种程度上相互呼应,共同勾勒出他对那个时代最深刻的感知。1991-1995年,这是一个充满着不确定性和转折的五年,我想知道鲍德里亚是如何在这些看似杂乱的碎片中,找到他独特的洞察力,并将它们转化为引人深思的文字。
评分这本《断片集:冷记忆(1991-1995)》的装帧本身就透露出一种沉甸甸的质感,仿佛一本承载了时代印记的旧相册,又像是某种神秘仪式的器皿。封面设计简洁却极具视觉冲击力,棱镜的意象隐喻着多重视角和破碎的现实,让人在翻开前就已进入一种沉思的状态。我一直对让·鲍德里亚的哲学思想充满好奇,尤其是他关于符号、仿真和消费社会的反思。尽管我尚未深入阅读这本书的具体内容,但仅从书名和作者的名号,就能预感到这将是一次精神上的探险。1991-1995年,这是一个在全球范围内充满变革的时期,冷战刚刚结束,信息技术开始萌芽,消费主义的浪潮愈演愈烈。鲍德里亚在这个时间段的思考,想必会捕捉到那些隐藏在社会表象之下的深刻症结。我期待着在这本书中,通过他独特的碎片化叙事,去理解那些“冷记忆”所承载的、被遗忘却又深刻影响着我们当下的信息和情感。它不仅仅是一本书,更像是一个思想的实验室,等待着我去探索,去解构,去重构。
评分读到《断片集:冷记忆(1991-1995)》这个书名,脑海中瞬间涌现出一种既熟悉又陌生的感觉。鲍德里亚的名字,总是伴随着一种难以捉摸的智慧和对现代性的尖锐剖析。我记得他的《消费社会》和《拟像与仿真》,那些论述像一把手术刀,精准地解剖了我们所处的这个由符号和影像构筑的超现实世界。而“断片集”的命名,预示着一种非线性、跳跃式的思维方式,这恰恰是鲍德里亚哲学的一大特色。我设想,这本集子可能收录了他在此期间一些零散的思考、随笔,甚至是一些未曾正式发表的观点。这些“冷记忆”,或许不是那种温暖的情感回忆,而是那些被冰封、被忽略、却又在某个时刻会重新浮现的思想火花。1991-1995年,这段历史的空白期,正是我们这个时代诸多矛盾和冲突开始显现的时期。我很想知道,鲍德里亚是如何在这些碎片化的观察中,捕捉到时代脉搏的跳动,以及他如何用他那极具辨识度的语言,将这些复杂的思绪呈现出来。
评分“棱镜精装人文译丛”这个系列,一直是我关注的焦点,它所引进的书籍,大多具备着深厚的思想底蕴和独特的文化视角。而《断片集:冷记忆(1991-1995)》这个书名,更是激起了我强烈的好奇心。鲍德里亚,这位后现代思想的巨擘,他的每一次发声都足以引起学界的震动。我一直认为,他的文字并非是线性的叙事,而更像是一系列精巧的陷阱,引诱读者进入一个由符号和意义构建的迷宫。这次以“断片集”的形式呈现,更是将这种不确定性和多义性推向了极致。我想象中的“冷记忆”,或许不是什么感性的伤怀,而是他对那个特定年代,那些正在发生的、或者已经过去但依旧具有影响力的事件、思潮、文化现象的冷静观察和深刻剖析。1991-1995年,恰逢世界格局剧变,科技飞速发展,消费主义文化全面渗透的时期,鲍德里亚在这个节点上的思考,无疑具有特殊的意义。我非常期待,能够在这本“断片集”中,感受到他独特而锐利的目光,捕捉到那些被淹没在信息洪流中的真实。
评分这本书的封面设计,尤其是那个“棱镜”的元素,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它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装饰,更像是对书中内容的隐喻——多角度的审视,以及对现实世界不同侧面的折射。鲍德里亚的作品,我一直觉得读起来需要一种特别的心境,它不像通俗读物那样易于消化,而是需要读者沉下心来,跟着他的思路去思考,去质疑。这次的《断片集:冷记忆(1991-1995)》,听名字就充满了探索的意味。“冷记忆”这个词,给我一种既疏离又迫近的感受,仿佛是那些被时间冷却,但又潜藏着巨大能量的过去片段。我猜想,这或许是他对那个特定时期,那些被主流话语所忽略,却又在潜意识中影响着我们的事件、观念或情绪的私人记录。1991-1995年,这是一个新旧世界交替的关键节点,信息爆炸的开端,全球化进程的加速,这些都为鲍德里亚提供了丰富的思考素材。我非常期待,能在这些“断片”中,发现他独特的视角,以及他对我们当下所处世界的深刻洞察。
评分波德里亚曾回顾道:“在20世纪60年代我进入大学,但那是一条迂回进入的路。总之,就正常的职业生涯来说,我总是没有命中目标,其中包括我从来没有升到教授”,然而,“这就是我所要的。这是我自己的游戏,我想说,我要的是某种程度的自由。”由此,足见他在体制内来“反体制”的革命态度,尽管他曾千方百计地要挤进学术体制之中,而且始终生活在其中,并在这个“学术共同体”中得到了基本的认同。
评分让·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又译吉恩·布希亚、让·波德里亚等。法国哲学家,现代社会思想大师,知识的“恐怖主义者”。他在对于“消费社会理论”和“后现代性的命运”的研究方面卓有建树,在20世纪80年代这个被叫做“后现代”的年代,让·鲍德里亚在某些特定的圈子里,作为最先进的媒介和社会理论家,一直被推崇为新的麦克卢汉。
评分波德里亚生长于法国传统家庭,祖父是农民,父母是公务员。他是家族中上大学的第一人,在巴黎获得了社会学博士学位。
评分京东商城的东西太多了,比淘上的东西还要多,而且都是正品~~~~~~~~书很好,我已经快速读一遍了在商店里我们可以看看新出现的商品,不一定要买但可以了解他的用处,可以增加我们的知识广度,扩宽我们的视野,同时随着社会的发展,科技不断更新,新出现的东西越来越多,日益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使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精彩,而我们购物要根据自己的情况分析,不要买些外表华丽而无实际用处的东西,特别是我们青少年爱对新生的事物好奇,会不惜代价去买,这是我们要注意的!京东商城的东西太多了,比淘上的东西还要多,而且都是正品,我经过朋友的介绍来过一次,就再也没有去过别的购物网站了。书不错 我是说给懂得专业的人听得 毕竟是小范围交流 挺好,粘合部分不是太好,纸质还是不错的,质量好,封装还可以。虽然价格比在书店看到的便宜了很多,质量有预期的好,书挺好!之前老师说要买 但是是自愿的没买 等到后来说要背 找了很多家书店网上书店都没有 就上京东看看 没想到被找到了 好了,我现在来说说这本书的观感吧,一个人重要的是找到自己的腔调,不论说话还是写字。腔调一旦确立,就好比打架有了块趁手的板砖,怎么使怎么顺手,怎么拍怎么有劲,顺带着身体姿态也挥洒自如,打架简直成了舞蹈,兼有了美感和韵味。要论到写字,腔调甚至先于主题,
评分主要中文版著作:
评分但是最后一页已经在我们指尖凋谢;
评分让·波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1929-2007),1929年7月29日出生于法国兰斯(Reims ),西方著名哲学家、社会学家。常被误认为是后现代主义者,实际不然,他批判过福柯等后现代主义,明确表明自己不是一个后现代主义者。
评分或许中国人很难感受到“上帝死了”这句话的重量。在几千年的文化当中,从始至终,中国人似乎并没有一个绝对的神祗,相反,宗教更仿佛是一种聚合人心的工具,却从来没得到过真正掌握话语权的阶层的信任。“子不语”就很明显地表明了知识分子对鬼神的态度——知之不详,不如敬而远之。而诸如各种关于“天”的说法,例如“奉天承运”或者“老天有眼”,实际上就像朱熹所言,“天”、“帝”、“道”、“理”都是同一本体的不同称呼,都是不具有人格色彩的客观规律集合。
评分非常棒的书籍,内容详实,装帧精美,绝对值得推荐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内容均为互联网搜索引擎提供的公开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储任何数据与内容,任何内容与数据均与本站无关,如有需要请联系相关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于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6 book.cndgn.com All Rights Reserved. 新城书站 版权所有




![世界少年文学精选·名家导读本:柳林风声 [11-14岁]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qciss.net/11485494/53a7c2c6Na9139a06.jpg)


![李拉尔的故事(套装共4册) [3-6岁]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qciss.net/11752271/55cdb60bNe2038de5.jpg)



![托马斯和朋友原著绘本(套装共6册) [3-7岁]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qciss.net/11908979/571d8132N6c168361.jpg)





![世界儿童文学传世经典-鲁滨孙漂流记 [9-14岁]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qciss.net/10836747/rBEQWFFQJdIIAAAAAAESWcRoAokAAC0DgGOsysAARJx876.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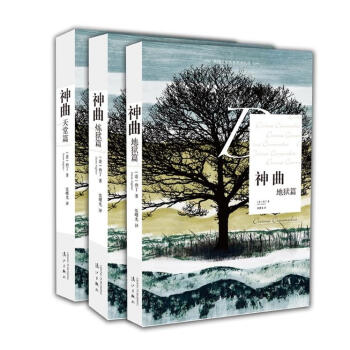
![世界伟人成长传记系列:可爱的“坏孩子”第2季(套装共10册) [7-10岁]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qciss.net/11235225/rBEhVVGyx68IAAAAAAIxjYrBQrYAAAFdQLm0a0AAjGl437.jpg)
![花朵开放的声音 [7-10岁]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qciss.net/11492562/53b61518Nfd4cd987.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