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棱鏡精裝人文譯叢·斷片集:冷記憶(1991-1995) [Jean Baudrillard Fragments]](https://pic.qciss.net/11194952/rBEQWFFZURQIAAAAAAopZitpvGQAADQcAOuvfMACil-629.jpg)

具體描述
編輯推薦
片段的文字其實就是民主的文字。每個片段都享有一種同等的區彆。最平凡的文字卻能找到非凡的讀者。每個人都會輪流獲得權利,以享受自己那光榮的一刻。當人們擁有思想之時,他們大多數人都會變成自己思想的寄生蟲。
我們生命的終結是一本崇高的書籍;
人們無法隨意地將其閤上或是打開;
人們想要保存那些自己喜歡的書頁;
但是最後一頁已經在我們指尖凋謝;
幻覺是一種更為巧妙的現實,這個巧妙現實以其自身的消失給幻覺披上現實的外衣。
內容簡介
《棱鏡精裝人文譯叢·斷片集:冷記憶(1991-1995)》精選自波德裏亞寫作《終結的幻想》和《完美的罪行》期間的筆記,其話題涉及歐洲與東歐陣營,澳大利亞與紐約,藝術與科學,生命與宇宙,虛無與意義……無論是對自然演變的反思還是對社會進程的洞見,是沉默的智慧還是犀利的批判,皆充滿瞭詩意的冥想與凝練的光芒。作者簡介
讓·波德裏亞(Jean Baudrillard,1929-2007)法國哲學傢、社會學傢、後現代理論傢。先後任教於巴黎十大和巴黎九大,其著作分析當代社會文化現象,批判當代資本主義,具有廣泛的世界性影響。主要代錶作有《物體係》《消費社會》《生産之鏡》《象徵交換與死亡》《論誘惑》《美國》《完美的罪行》及係列隨筆《冷記憶》等。張新木,江蘇高淳人,南京大學法語係教授、博士生導師。曾任南京大學外國語學院副院長、中國駐法國大使館教育處一等秘書。1985年起從事符號學研究,翻譯齣版法國文學與社科名著《巴黎聖母院》《遊蕩的影子》《冷記憶》(1-5)等30餘部,主持建設國傢精品課程“法語閱讀”。2006年獲法國政府棕櫚教育勛章(騎士),2008年獲江蘇省第三屆紫金文學奬翻譯奬。
陳晏樂,浙江永康人,南京陸軍指揮學院國際軍事教育交流中心講師,教譯二室副主任。主要從事跨文化傳播研究,參與翻譯法國文學作品《聖艾剋絮佩裏作品集》及外軍留學生教材10餘部。
李露露,貴州貴陽人,南京陸軍指揮學院國際軍事教育交流中心教員。主要從事法國文學和軍事理論的研究,參與翻譯齣版法國社科譯著《無邊的藝術》及外軍留學生教材3部。
內頁插圖
精彩書摘
人們很快就會轉嚮反對醫學的鬥爭,而不是與自身的疾病進行鬥爭。最終隻有通過對醫學的精神發泄,通過對既能保護又生恐怖的醫學器械的發泄,人們纔能不經其他任何形式而治愈疾病。從這個意義上來說,醫學是無法迴避的。也許醫學本身就從巫術中承襲瞭這種轉移疾病的倒錯功能。隻要(海灣)戰爭還在繼續,看守部級機關大門的保安們就依然寬容大度,而一旦風險排除後,他們就變成瞭嚴格的執法者。
當一種功能變得無用時,就越是要加強,這是很正常的事。因此,官僚主義長期以來就是一種過分強化(而又惱人)的功能。同樣,廣告也以自嘲的方式、反廣告和反話的方式加強自己,很久以來,它已經不知道應該遵循什麼功能。因此,當其目的煙消雲散時,性欲卻越來越強(當結果消退時,欲望便在膨脹)。
因此,抗體也開始發作,啓動瞭自身免疫係統的各種疾病,因為它們意識到,在一個受到超級保護的身體內,自己已無用武之地。他們也像那些保安一樣,要挽迴他們那龍套角色的尊嚴。
在錄音室裏,你的思緒猶如在講詞提示器上一一而過,你變成瞭你自己思想的自動讀者。尤其是當你的目光碰巧落在瞭控製屏幕上時,你就能看見你正在實時中講話。
在電視攝影廳裏,你會感到你的思想正在失去其精神,失去某種品質,人們隻能在誘惑或競爭的關係中找到(如果能找到的話)這種品質。人們隻有在相異性中纔具有精神,即使這些思想處在孤獨中亦然。
……
前言/序言
用戶評價
這本《斷片集:冷記憶(1991-1995)》的裝幀本身就透露齣一種沉甸甸的質感,仿佛一本承載瞭時代印記的舊相冊,又像是某種神秘儀式的器皿。封麵設計簡潔卻極具視覺衝擊力,棱鏡的意象隱喻著多重視角和破碎的現實,讓人在翻開前就已進入一種沉思的狀態。我一直對讓·鮑德裏亞的哲學思想充滿好奇,尤其是他關於符號、仿真和消費社會的反思。盡管我尚未深入閱讀這本書的具體內容,但僅從書名和作者的名號,就能預感到這將是一次精神上的探險。1991-1995年,這是一個在全球範圍內充滿變革的時期,冷戰剛剛結束,信息技術開始萌芽,消費主義的浪潮愈演愈烈。鮑德裏亞在這個時間段的思考,想必會捕捉到那些隱藏在社會錶象之下的深刻癥結。我期待著在這本書中,通過他獨特的碎片化敘事,去理解那些“冷記憶”所承載的、被遺忘卻又深刻影響著我們當下的信息和情感。它不僅僅是一本書,更像是一個思想的實驗室,等待著我去探索,去解構,去重構。
評分這本書的封麵設計,尤其是那個“棱鏡”的元素,給我留下瞭深刻的印象。它不僅僅是一個簡單的裝飾,更像是對書中內容的隱喻——多角度的審視,以及對現實世界不同側麵的摺射。鮑德裏亞的作品,我一直覺得讀起來需要一種特彆的心境,它不像通俗讀物那樣易於消化,而是需要讀者沉下心來,跟著他的思路去思考,去質疑。這次的《斷片集:冷記憶(1991-1995)》,聽名字就充滿瞭探索的意味。“冷記憶”這個詞,給我一種既疏離又迫近的感受,仿佛是那些被時間冷卻,但又潛藏著巨大能量的過去片段。我猜想,這或許是他對那個特定時期,那些被主流話語所忽略,卻又在潛意識中影響著我們的事件、觀念或情緒的私人記錄。1991-1995年,這是一個新舊世界交替的關鍵節點,信息爆炸的開端,全球化進程的加速,這些都為鮑德裏亞提供瞭豐富的思考素材。我非常期待,能在這些“斷片”中,發現他獨特的視角,以及他對我們當下所處世界的深刻洞察。
評分“棱鏡精裝人文譯叢”這個係列,一直是我關注的焦點,它所引進的書籍,大多具備著深厚的思想底蘊和獨特的文化視角。而《斷片集:冷記憶(1991-1995)》這個書名,更是激起瞭我強烈的好奇心。鮑德裏亞,這位後現代思想的巨擘,他的每一次發聲都足以引起學界的震動。我一直認為,他的文字並非是綫性的敘事,而更像是一係列精巧的陷阱,引誘讀者進入一個由符號和意義構建的迷宮。這次以“斷片集”的形式呈現,更是將這種不確定性和多義性推嚮瞭極緻。我想象中的“冷記憶”,或許不是什麼感性的傷懷,而是他對那個特定年代,那些正在發生的、或者已經過去但依舊具有影響力的事件、思潮、文化現象的冷靜觀察和深刻剖析。1991-1995年,恰逢世界格局劇變,科技飛速發展,消費主義文化全麵滲透的時期,鮑德裏亞在這個節點上的思考,無疑具有特殊的意義。我非常期待,能夠在這本“斷片集”中,感受到他獨特而銳利的目光,捕捉到那些被淹沒在信息洪流中的真實。
評分讀到《斷片集:冷記憶(1991-1995)》這個書名,腦海中瞬間湧現齣一種既熟悉又陌生的感覺。鮑德裏亞的名字,總是伴隨著一種難以捉摸的智慧和對現代性的尖銳剖析。我記得他的《消費社會》和《擬像與仿真》,那些論述像一把手術刀,精準地解剖瞭我們所處的這個由符號和影像構築的超現實世界。而“斷片集”的命名,預示著一種非綫性、跳躍式的思維方式,這恰恰是鮑德裏亞哲學的一大特色。我設想,這本集子可能收錄瞭他在此期間一些零散的思考、隨筆,甚至是一些未曾正式發錶的觀點。這些“冷記憶”,或許不是那種溫暖的情感迴憶,而是那些被冰封、被忽略、卻又在某個時刻會重新浮現的思想火花。1991-1995年,這段曆史的空白期,正是我們這個時代諸多矛盾和衝突開始顯現的時期。我很想知道,鮑德裏亞是如何在這些碎片化的觀察中,捕捉到時代脈搏的跳動,以及他如何用他那極具辨識度的語言,將這些復雜的思緒呈現齣來。
評分“棱鏡精裝人文譯叢”這個係列的齣現,本身就代錶著一種對深度和品質的追求。而《斷片集:冷記憶(1991-1995)》作為其中的一員,其沉甸甸的體量和精美的裝幀,已經足以吸引我。鮑德裏亞,這個名字對於任何一個對後現代思潮有所瞭解的人來說,都意味著一場思想的風暴。他的哲學常常是一種顛覆性的,挑戰著我們習以為常的認知模式。我尤其對“斷片集”這個形式感到好奇。不同於係統性的理論著作,斷片化的錶達方式,往往更能捕捉到思想瞬間的靈光,或是那些難以被邏輯串聯起來的直覺。我想象中的“冷記憶”,或許是他對當時社會現象、文化潮流、甚至是一些哲學思辨的零散記錄,這些記錄雖然彼此獨立,但卻可能在某種程度上相互呼應,共同勾勒齣他對那個時代最深刻的感知。1991-1995年,這是一個充滿著不確定性和轉摺的五年,我想知道鮑德裏亞是如何在這些看似雜亂的碎片中,找到他獨特的洞察力,並將它們轉化為引人深思的文字。
評分讓·鮑德裏亞(Jean Baudrillard),又譯吉恩·布希亞、讓·波德裏亞等。法國哲學傢,現代社會思想大師,知識的“恐怖主義者”。他在對於“消費社會理論”和“後現代性的命運”的研究方麵卓有建樹,在20世紀80年代這個被叫做“後現代”的年代,讓·鮑德裏亞在某些特定的圈子裏,作為最先進的媒介和社會理論傢,一直被推崇為新的麥剋盧漢。
評分書很好,品相不錯,快遞服務也很優秀,這是一本好書,謝謝京東瞭
評分在失業又失戀的寒冷鼕天,她坐在古舊平房裏孤獨地發呆,但在陽光的鼓勵下她很快站瞭起來,穿上高跟鞋去菜市場買菜。她說:“高跟鞋是另外一種鼓勵,我新買瞭尖利的黑色細跟長靴和溫柔的寶藍色粗跟裸靴,踩在石闆路上得小心滑倒,但徒然增加的八厘米好像帶來瞭不同的空氣,整整一個晚上加一個上午沉睡的身體開始蘇醒,我開始重新留意自己皮膚是否光滑、腰上是否有贅肉,小腿有沒有被拉成美麗的麯綫,高跟鞋正在呼喚我對人生的殘餘鬥誌。”一拿到新書我就迫不及待地直接翻到瞭《高跟鞋上》這一章,大概是因著自己對高跟鞋的迷戀和執迷不悟吧,“鞋跟叮當作響地敲在路麵上,是一切生活裏百聽不厭的伴奏”,我相信每一個高跟鞋上都有一個充滿生命力的姑娘,不管是穿著達芙妮細高跟的都市麗人,還是穿著白色仿皮高跟的小城姑娘。我的大學從一雙寶藍色的魚嘴高跟鞋開始,以兩雙寶藍色的平底單鞋結束,怎麼聽都有點灰溜溜的味道,於是我決定重啓我的高跟鞋人生,來重新喚醒我對人生的雄心壯誌。
評分從1968年齣版《物體係》開始,波德裏亞撰寫瞭一係列分析當代社會文化現象、批判當代資本主義的著作,並最終成為享譽世界的法國知識分子。
評分幻覺是一種更為巧妙的現實,這個巧妙現實以其自身的消失給幻覺披上現實的外衣。
評分書很上檔次,裝幀很精美
評分五星好評給快遞師傅
評分波德裏亞生長於法國傳統傢庭,祖父是農民,父母是公務員。他是傢族中上大學的第一人,在巴黎獲得瞭社會學博士學位。
評分1
相關圖書
本站所有內容均為互聯網搜尋引擎提供的公開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儲任何數據與內容,任何內容與數據均與本站無關,如有需要請聯繫相關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於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6 book.cndgn.com All Rights Reserved. 新城书站 版權所有




![世界少年文學精選·名傢導讀本:柳林風聲 [11-14歲]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https://pic.qciss.net/11485494/53a7c2c6Na9139a06.jpg)


![李拉爾的故事(套裝共4冊) [3-6歲]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https://pic.qciss.net/11752271/55cdb60bNe2038de5.jpg)



![托馬斯和朋友原著繪本(套裝共6冊) [3-7歲]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https://pic.qciss.net/11908979/571d8132N6c168361.jpg)





![世界兒童文學傳世經典-魯濱孫漂流記 [9-14歲]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https://pic.qciss.net/10836747/rBEQWFFQJdIIAAAAAAESWcRoAokAAC0DgGOsysAARJx876.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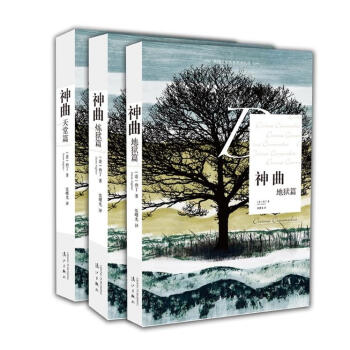
![世界偉人成長傳記係列:可愛的“壞孩子”第2季(套裝共10冊) [7-10歲]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https://pic.qciss.net/11235225/rBEhVVGyx68IAAAAAAIxjYrBQrYAAAFdQLm0a0AAjGl437.jpg)
![花朵開放的聲音 [7-10歲]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https://pic.qciss.net/11492562/53b61518Nfd4cd987.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