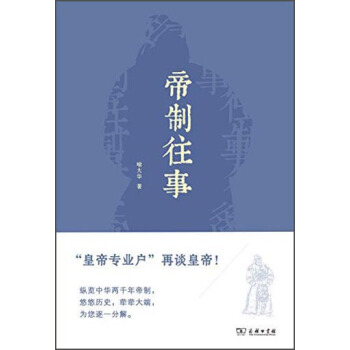具体描述
编辑推荐
异端与正统的斗争不是科学与迷信的斗争,而是两种科学之间的竞争。“人文探索”是什么?
谁要想进入人类文明的细节,谁就开始了一次别开生面的探索。在这里,即使是一只茶杯,也有着比任何一个王朝还要漫长的历史,它们经历着文明、塑造着文明、甚至本身就构成着文明。
在众所周知的事物之上发现新的事物,在耳熟能详的话题之内发现新的路向,“人文探索”让每个人开始一次知识的考古。
本书向人们展现了过去两千年间西方社会中的异端、分裂派和异议派群体。作者从基督教早期深有影响的诺斯替派讲起,直至现代的各类宗派。内容涉及多种多样的“异端”形象,包括那些为信仰而准备殉道的人以及行为“怪异”的宗派。此外,本书还考察了异端产生的社会政治条件,并展现了那些“异端”是如何被“判为”异端,以及他们所接受的惩罚——囚禁和火刑。本书内容丰富,论述透彻,具有很强的可读性。
内容简介
这本通俗简明的小书向人们展现了过去两千年间西方社会中的异端、分裂派和异议派群体。作者从基督教早期深有影响的诺斯替派讲起,直至现代的各类宗派。内容涉及多种多样的“异端”形象,包括那些为信仰而准备殉道的人以及行为“怪异”的宗派。这些“异端”群体对基督教会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一方面教会要极力坚持正统观;一方面在这些不同观念的刺激之下,一些基本的观念得以被深入讨论。此外,本书还考察了异端产生的社会政治条件,并展现了那些“异端”是如何被“判为”异端,以及他们所接受的惩罚——囚禁和火刑。
作者简介
吉尔·R.埃文斯(Gill R.Evans),剑桥大学历史学教授,主要研究中世纪的神学和知识分子。她写过一系列关于奥古斯丁、大格利高利和安瑟伦等中世纪学者的著作,其代表作品有《中世纪的神学和法律》(2002年),《中世纪的信仰》(2002年),《中世纪的神学和哲学》(1993年)等。内页插图
目录
前言第一章 合一的重要性
达成共识
教皇制
异教徒手中的圣经
容许存在异议的领域
第二章 正统的边界:信仰
《使徒信经》
《尼西亚信经》
要理问答
对象错置的崇拜和滥用上帝之名
信仰在历史中“发展”吗?
信经的内容与正统的问题
第三章 正统的界限:教会的建制
教会外围的“混乱”
秩序(Orderliness)
事工和建制
严格主义者的辩论
分裂论
大流散
正统实践
第四章 异端的分类
基督教可以引入古代哲学的哪些内容?
道成肉身和基督论
奥古斯丁的三个问题
复活节之争
化质说的教义
1054年和东西部的大分裂
从教派到“宗派身份”(Confessional Identity)
名之威力
非信徒的种类
给涉嫌的异端定罪
批判文学的出现
第五章 异端和社会的挑战
大众异端:反制度异议者的辩护
异议之路(The Road to Dissent)
瓦勒度派
约翰·威克利夫和罗拉德派的运动
约翰·胡斯
胡斯“运动”
中世纪之后的社会影响
第六章 善与恶
中世纪的二元论
第七章 对异端的处理
大学布道
异端自己的宣讲
十字军
宗教裁判所
权力平衡的改变
忍受差异
结语
注释
进一步阅读书目
索引
精彩书摘
第一章 合一的重要性许多世纪以来,基督教会想合一的外在原因一直不断发展变化。但是,在各个时代,想要合一的更深层次的原因却没有变化,具有一贯性。基督教开始时必须从犹太教和当时多神崇拜的异教信仰中分离出来。年轻的教会在不断成长的过程中,人数逐渐增多,结构日趋复杂,为了使基督教信仰不致分崩离析,沦为成千上万种不同的形态,教会也需要处理实际问题,来控制它本身的变化和发展。
这些都是有关群体需要考虑的要素。对当代西方世界的许多基督徒来说,个人灵魂与上帝的关系似乎最为重要,但是相对而言,这只是近年来才强调的内容。16世纪及之后西方的辩论才把该思想带进了信徒的视野,形成了宗教改革(Reformation)的教会。一开始,只是出现了偏离教会大公性或普世性的主张。许多宗教改革领袖排斥当时“可见”的普世教会,视之为被敌基督腐蚀的教会,并主张真正的教会是不可见的,只有上帝知道。其他人则指向自己拥戴的可见教会,视之为真正的教会。
因此,群体感开始减弱018世纪的敬虔主义(pietism)和启蒙运动(Enlightenment)鼓励信徒相信,重要的是个人的委身而非成为某个“可见”普世教会的一员(也不需要二者得兼)。
前言/序言
用户评价
阅读这本著作,仿佛进入了一个庞大而错综复杂的迷宫,每条路径都通向一个需要深度思考的岔路口。我必须承认,某些章节的密度极高,需要边读边做大量的标记和笔记,否则很容易在作者那绵密如织的论证链条中迷失方向。这本书的叙事节奏张弛有度,在铺陈宏大的时代背景之后,总会聚焦于某个关键人物或某场决定性的辩论,这种对焦和散焦的交替运用,极大地增强了阅读的戏剧张力。作者对于“边缘”如何影响“中心”的模式分析得极为精辟,他展示了那些最初被排斥和妖魔化的思想,是如何在不经意间,重塑了主流的认知框架。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他对于概念演变路径的追踪,一个词汇或一个理念,在不同时代、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意义漂移和意义重构,被他描绘得栩栩如生,这对于理解当代思想的复杂性极具启发性。它是一本需要反复回味的书,初读领略其骨架,再读才能品味出其血肉。
评分老实说,这本书的阅读门槛着实不低,它要求的不仅仅是耐心,更是一种对复杂思想体系的消化能力。我得承认,有好几处我不得不停下来,反复咀嚼那些长而复杂的句子,它们像是精密编织的逻辑网,稍微一分心就可能错失了关键的连接点。这本书的厉害之处在于,它能将看似风马牛不相及的领域——比如早期的形而上学辩论与后来的政治运动——巧妙地编织在一起,揭示出其背后共享的同一股思想暗流。作者似乎对“何为正统”这个概念本身抱有一种近乎偏执的解构欲,他层层剥开社会如何构建权威、又如何利用这种权威来压制异见的机制。其中涉及到的一些古代文本的引述和解读,如果缺乏一定的背景知识,初次接触可能会感到有些晦涩难懂,但这恰恰是其魅力所在,它拒绝迎合浅尝辄止的读者,更像是一本写给“求知者”的密码本。它让你意识到,历史上的每一次思想冲突,都不是简单的善恶对立,而是多方力量在真理解释权上的残酷角力。
评分这本书的语言风格是内敛而富有穿透力的,它没有那种为吸引眼球而采用的夸张修辞,但每一个选择的词汇都像是经过千锤百炼的利刃,直指问题的核心。它像是一位技艺高超的钟表匠,向你展示了时间观念是如何被一步步打磨成形的。我尤其欣赏作者在叙述过程中所展现出的那种深沉的“怀疑精神”,他似乎对一切既定的“绝对真理”都抱持着一种健康的疏离感。书中对思想史的梳理,绝非简单的编年史,而是对“认知冲突”的深入解剖,探讨了人类在面对未知和不确定性时,是如何通过建立和摧毁思想体系来寻求心理安慰的。这种探究深入到了人类的心理层面,使得书中的历史事件不再是冰冷的记录,而成了人类永恒的困境和挣扎的缩影。对于希望理解“思想是如何改变世界”的读者来说,这本书提供了一个无比清晰和深刻的观察窗口,它教会我们,真正的进步往往诞生于那些不被理解和接纳的角落。
评分这本书的阅读体验简直是一场思想的马拉松,让人在字里行间不断地与自身既有的认知进行辩论和重塑。作者的叙事手法非常高明,他并不急于给你一个明确的“是”或“非”,而是像一个经验丰富的考古学家,小心翼翼地挖掘出那些被时间尘封的观念碎片,并将它们重新排列组合。我特别欣赏他对历史进程中那些“边缘声音”的关注,那些往往被主流叙事所淹没的微弱却坚韧的呼喊。比如,他深入探讨了在某个特定历史时期,一种被视为异端的思想是如何从一粒微不足道的火星,最终演变成足以燎原的野火,这不仅仅是历史事件的罗列,更是一种对人类心智活动深层驱动力的哲学探讨。书中的论证结构严密得令人赞叹,每一个看似跳跃的观点背后,都有着详实的文献支持和逻辑推导,让你不得不跟随他的思路前行,即使你内心深处仍旧抱持着怀疑。这种挑战性的阅读过程,虽然需要极高的专注度,但回报也是巨大的——它强迫你跳出舒适区,去审视那些你曾深信不疑的基础假设。读完后,我感觉自己看待世界的方式被润物细无声地调整了一个微妙的角度,不再那么轻易地接受既定的真理。
评分这本书给我带来的最深刻感受,是一种关于“思想韧性”的震撼教育。我常常在想,那些被时代判了死刑的观点,是如何在地下世界悄悄地延续生命力的?作者以一种近乎诗意的笔触,描绘了那些曾经被视为洪水猛兽的思想,它们是如何在知识的真空地带,如同顽强的种子一般,等待下一次破土而出的契机。它不是一本标准的历史教科书,它更像是一部思想的“生物志”,记录了不同观念形态的诞生、繁衍、衰亡和变异过程。阅读过程中,我特别留意了作者在处理那些极具争议性的人物或学说时的措辞,他很少使用道德审判的语言,更多的是一种冷峻的观察和对内在逻辑的挖掘。这种近乎客观的疏离感,反而让人能够更心无旁骛地去探究这些思想的内在魅力和历史必然性。它迫使我反思,今天我们所珍视的“常识”,在未来,又将如何被重新审视和挑战?这种跨越时空的心灵对话,令人沉醉。
评分"[SM]和描述的一样,好评! 上周周六,闲来无事,上午上了一个上午网,想起好久没买书了,似乎我买书有点上瘾,一段时间不逛书店就周身不爽,难道男人逛书店就象女人逛商场似的上瘾?于是下楼吃了碗面,这段时间非常冷,还下这雨,到书店主要目的是买一大堆书,上次专程去买却被告知缺货,这次应该可以买到了吧。可是到一楼的查询处问,小姐却说昨天刚到的一批又卖完了!晕!为什么不多进点货,于是上京东挑选书。好了,废话不说。好了,我现在来说说这本书的观感吧,一个人重要的是找到自己的腔调,不论说话还是写字。腔调一旦确立,就好比打架有了块趁手的板砖,怎么使怎么顺手,怎么拍怎么有劲,顺带着身体姿态也挥洒自如,打架简直成了舞蹈,兼有了美感和韵味。要论到写字,腔调甚至先于主题,它是一个人特有的形式,或者工具;不这么说,不这么写,就会别扭;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腔调有时候就是“器”,有时候又是“事”,对一篇文章或者一本书来说,器就是事,事就是器。这本书,的确是用他特有的腔调表达了对“腔调”本身的赞美。|发货真是出乎意料的快,昨天下午订的货,第二天一早就收到了,赞一个,书质量很好,正版。独立包装,每一本有购物清单,让人放心。帮人家买的书,周五买的书,周天就收到了,快递很好也很快,包装很完整,跟同学一起买的两本,我们都很喜欢,谢谢!了解京东:2013年3月30日晚间,京东商城正式将原域名360buy更换为jd,并同步推出名为“joy”的吉祥物形象,其首页也进行了一定程度改版。此外,用户在输入jingdong域名后,网页也自动跳转至jd。对于更换域名,京东方面表示,相对于原域名360buy,新切换的域名jd更符合中国用户语言习惯,简洁明了,使全球消费者都可以方便快捷地访问京东。同时,作为“京东”二字的拼音首字母拼写,jd也更易于和京东品牌产生联想,有利于京东品牌形象的传播和提升。京东在进步,京东越做越大。||||好了,现在给大家介绍两本本好书:《谢谢你离开我》是张小娴在《想念》后时隔两年推出的新散文集。从拿到文稿到把它送到读者面前,几个月的时间,欣喜与不舍交杂。这是张小娴最美的散文。美在每个充满灵性的文字,美在细细道来的倾诉话语。美在作者书写时真实饱满的情绪,更美在打动人心的厚重情感。从装祯到设计前所未有的突破,每个精致跳动的文字,不再只是黑白配,而是有了鲜艳的色彩,首次全彩印刷,法国著名唯美派插画大师,亲绘插图。|两年的等待加最美的文字,就是你面前这本最值得期待的新作。《洗脑术:怎样有逻辑地说服他人》全球最高端隐秘的心理学课程,彻底改变你思维逻辑的头脑风暴。白宫智囊团、美国FBI、全球十大上市公司总裁都在秘密学习!当今世界最高明的思想控制与精神绑架,政治、宗教、信仰给我们的终极启示。全球最高端隐秘的心理学课程,一次彻底改变你思维逻辑的头脑风暴。从国家、宗教信仰的层面透析“思维的真相”。白宫智囊团、美国FBI、全球十大上市公司总裁都在秘密学习!《洗脑术:怎样有逻辑地说服他人》涉及心理学、社会学、神经生物学、医学、犯罪学、传播学适用于:读心、攻心、高端谈判、公关危机、企业管理、情感对话……洗脑是所有公司不愿意承认,却是真实存在的公司潜规则。它不仅普遍存在,而且无孔不入。阅读本书,你将获悉:怎样快速说服别人,让人无条件相信你?如何给人完美的第一印象,培养无法抗拒的个人魅力?如何走进他人的大脑,控制他们的思想?怎样引导他人的情绪,并将你的意志灌输给他们?如何构建一种信仰,为别人造梦?[SZ]"
评分了解异端的历史,有参考价值
评分護教學(三)
评分挺不错的。希望大家多读书读好书。
评分帮朋友买的,活动时购入,还不错。
评分这本通俗简明的小书向人们展现了过去两千年间西方社会中的异端、分裂派和异议派群体。
评分但如今, 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
评分2.创世纪开首几章留给我们甚么关于神的「双胞眞理」?每项真理是透过甚么事件强调的?
评分不知道讲什么的,好像是最后一本啊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内容均为互联网搜索引擎提供的公开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储任何数据与内容,任何内容与数据均与本站无关,如有需要请联系相关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于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6 book.cndgn.com All Rights Reserved. 新城书站 版权所有




![独立宣言:一种全球史 [The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A Global History]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qciss.net/11418670/rBEhWlMhI34IAAAAAACzl7uu9jwAAJ9ggJN5G8AALOv332.jpg)